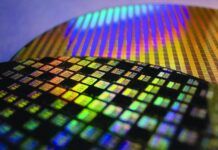卡巴拉,kabalah,在希伯來語中意為接受,這是一套為維護猶太教權威而出現的信條。卡巴拉在通俗文化中的曝光量非常高,就算對於猶太教一無所知的人,只要看過一些動畫一些影集,或是玩過一些遊戲看過一些網文,就不會對所謂的卡巴拉生命之樹過於陌生。雖然被以所謂「猶太密教」之名廣為人知,但與其對應的「猶太顯教」相比,人們反而更熟悉它一些:這點聽起來頗具諷刺意味。相比之下,可能因為沒有被金色黎明(Golden Dawn)盯上的緣故,與之同根同源的另外兩大亞伯拉罕體系的學說就不出名——動畫里面用爛的偽狄奧尼修斯天使階級,或純粹以阿拉丁神燈面目示人的巨靈——恐怕這也和後兩者的載體在今天多是其他方面的刻板印象有關。也因此,猶太神秘主義的一個主要分支——可能今日就只剩這個分支,其餘皆被其消滅——卡巴拉被神化,甚至常常扮演了少數人的真理,或是狂人的智慧。
因為對其的神化愈演愈烈,對此好奇的人不少,在通俗文化領域有不少普及,不過其中大部分僅僅是對結論的復述。對其歷史,人知道的很少,一方面是不感興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兩千年前的內容與如今人們熟知的大相逕庭。這也難怪該歷史雖然並不是它研究的內容那樣的「密教」,但反而只有特定小眾圈子的人知道它了。對其的了解基本上只停留在學院內部,輻射范圍有限。
現代猶太神秘主義歷史最重要的著作是Gershom Schelom的《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 mystique judaisme》,後世論及此歷史的作品勢必會引用或以此為基礎進行修正。該書有中文譯本《猶太神秘主義主流》是上個世紀翻譯的,有不少刪減,沒有再版。對於曾閱讀過此書的人可以不必看這篇文章,因為內容基本一致。由於並非是學院出身,所以可能概念混淆,論述既不科學也不嚴謹,加上本身猶太思想一片混亂,因此此處的描述只能算是一種個人感受,夾雜一些評斷,還望見諒。不同派系解釋差異難以避免,是故必定與對此熟知者所知有所不同。由於是憑借印象對其梳理,許多曾經看過的論文如今已找不到,但也不想花費心思做成嚴肅的論文,因此沒有參考文獻一條。還望包容。
此處所舉之神秘主義一詞為mysticism,一些內容應被視作是某種內部信念esotericism,並非被市場和大眾稱作所謂神秘學的occultism,而且此處所言之卡巴拉與金色黎明的赫爾墨斯卡巴拉有相當大的差別,後者除了用了這個名字以及一點點要素以外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
本文和所謂神秘學沒有任何關系,也和傳教沒有任何關系,煩請評論時帶有些許耐心。

偽經
猶太神秘主義與古代信條密不可分。從某種角度來說,任何形式的古代信條的核心都包含神秘主義,因為神秘主義涉及真理的直觀與真理的宣告,而各種形式的奇跡和傳說則為真理所發,是神秘主義的表現和外皮。
正因其關系如此緊密,因此在談及信條歷史時不能繞開神秘主義歷史,同樣,談及神秘主義也勢必會牽涉信條歷史。不過西歐的宗教改革是一個例外。這個改革雖然涉及真理宣告,但是真理於此已從啟示的,超越人的真理變成了人的,服從理性並接受理性改造的真理。因為這一改變,該運動與神秘主義沒有一點聯系,但卻對西方神秘主義思想本身產生了巨大影響。所幸此運動對於猶太神秘主義思想沒有造成根本性的改變,因此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會較少談到。
如同之前所言,對於這方面的討論繞不開信條自身的發展歷史,因此若要對猶太神秘主義的歷史進行討論,那麼就必須將目光投向兩千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觀察其最原始的形態。
盡管考古發現的第一聖殿時期寫有大祭司祝福的護身符可能涉及最早的猶太神秘主義信念,但因為缺乏當時的文本描述,對於這個階段的了解並不足夠。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部分信條也有部分影響或延續到後世。而作為第一聖殿時期最重要的內容,即聖殿和祭祀,不僅滲透了先知書,還通過其覆滅而成為後世猶太神秘主義中一組重要的象徵。
巴比倫流亡以及重建第二聖殿意味著一個新世代的開始,並且經過巴比倫與波斯直到羅馬的整合,在這個漫長的時間跨度中,猶太信條自身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猶太神秘主義也在這個期間顯露雛形。巴比倫時期猶太社會中涌現的智者文學以說教為主要目的,通過歸納總結的方式,智者文學將實踐律法的美德與阻止實踐的惰性對比,以達到教化目的。但是同時在這個時期,亞述的唯一神觀念,巴比倫的天文學和惡魔學說,以及波斯人對於天使並思言行上的善惡的思考與帶有明顯虔敬特徵的猶太智者文學結合起來。由此,最早的猶太神秘主義思想同原始猶太教一樣,在其中初具雛形,其中不少借著先知傳統,以默示題材文本的形式留存下來。
這些文本中有不少以偽經(Pseudepigraphos)這個稱呼為今人所知。
偽經是基督教教父對聖經正典以後,成書於聖殿猶太教時期的神秘文本的概稱,其中大部分文本集中寫作於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後三世紀。這些文本有些來自於希臘化猶太世界,有些則來自於保守猶太世界。保守猶太世界的文本創作於巴比倫及巴勒斯坦,而巴比倫地區的文本通常比較古老,稍晚些塔木德世代的文本沒有被收錄。這些偽經保留了相當原始的文學形式,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聖經中的智慧文學與先知文學的延伸。《偽經》的作者聚焦於我們所在的世界和歷史,並以此為舞台上演他們所希望的故事。
和先知時代相比,他們大部分喜歡用創世和早年間發生的事情來解釋現在——通常是非常古老的時代,亞當,諾亞,亞伯拉罕,或是摩西,他們間接或直接的預言當下,並通過干預神的決定而導致當今或是未來的局面。因為亞當的罪過,人受到譴責,因為諾亞時代的人類,人學會不義,因為亞伯拉罕的約定,猶太人受環境排斥,因為摩西時代的金牛犢,猶太人必須流亡。而往往這些遠古錯誤也包含了解決自身的方案,這些都一並隱藏在創世之中,而修正伴隨著的是再創世——這構成了猶太神秘主義的一個千年不變的核心,包括基督教也繼承了這點。
另外還有一些作者以某個著名先知或重要人物之名,寫下一串模糊晦澀的異象。這些異象揭示了此時的困境,並以日後的賞報勉勵時人。實際上這類偽經專注於末世論和救世主。毫不意外的,這類文本自動與此前創始論的文本掛鉤,甚至主動引用後者。與創世的奧秘平行,這些文本沉迷於揭露已有或現在的奧秘秩序。不再是從原初——或者說混沌,希伯來人沒有基督教宣導的從虛無中創造的理念,只有希臘化猶太人持虛空創造的觀念——發散萬物,而是現階段萬物的秩序和規則。至於未來如何,這些文本通過草草帶過這種方式承認自己的無知:通常末日的描述不是模糊不清就是晦澀難懂。
偽經作者盡管對他們所見所知描述的豐富異常,但他們從沒有提到他們是如何得知這些內容的。或許我們可以參考先知書,不僅因為他們和先知書時代接近,內容相近,也因為這些作者經常託名或是暗示這來自先知。作為這方面文本的代表,《哈諾克書(Hanokh)》不得不提。盡管這本書在早期被視作正典並在死海社群使用,但很遺憾的是,它最終沒有被大部分群體接納。同樣待遇的還有《厄斯德拉四書(Ezra)》,一部目前只在敘利亞語和亞美尼亞語中還能找到完整版本的書。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哈諾克書在歷史上主要是第二聖殿巴勒斯坦傳統流行,巴比倫傳統拒不承認,而哈諾克與梅塔特隆的結合至少是四世紀以後的事情了。
這兩部書都托先知為作者,以先知書的筆調進行描寫,其內容包含了創世,萬物秩序,以及末日審判三大關鍵節點。哈諾克提到了邪惡天使亞扎澤勒(Azazel)以解釋惡的由來,在這里惡者僅僅是誘惑者,而原初的惡來自人自身。厄孜拉則強調了當下受苦的必然,勉勵人轉向於神明,並預示了未來聖殿重建以及末日審判帶來。這些書都無一例外的指出,啟示來自天使傳授,而神直接抓住了他們,如同伊赫梅雅烏(Yirmeyahu)先知一樣,在這件事上非常被動,即使是向神請求主動進入天界,也是因為神回應而實行。這與後面的文本大相逕庭。
另外,在這個時期,對於惡魔的描述也泛濫起來,這在之前聖經世代並不明顯。智慧文學中對於人劣根性的描述,聖經中撒殫作為誘惑人犯罪者現身,以及惡魔對人的迫害與對神的忤逆,使得這個世代對於惡魔的描述變得抽象起來,甚至出現了將惡魔對應惡意的趨勢。

耶路撒冷塔木德及其他
基本上猶太學者在介紹猶太神秘主義思想時,都是從這個世代開始的,而最早如此進行的就是德國猶太學者Gershom Schalom。這麼做的理由很簡單,首先是因為從這里開始,猶太神秘主義只為猶太人服務,不再和基督教有關系,其次,則是因為猶太教在傳承過程中又經歷了一次斷代,人們熟悉的現代猶太教在追溯根源的時候會追溯到這個時刻,即耶路撒冷覆滅後,大經師扎凱之子約哈難在耶夫尼重建猶太教。
聖殿毀滅與基督教興起,這兩件大事決定了後續猶太神秘主義的走向。聖殿在古代猶太習俗中有非常高的地位,因為它是神的居所,是神臨在之所。這意味著聖殿是神在地上的有形顯現,眾人依靠聖殿的各項功能與活動實現個人與族群的神秘實現,尤其是從污穢狀態中解脫以及獲得神光的祝福,亦即猶太人的存續。換言之:聖殿約等於神。這也使得在後續猶太神秘主義中關於聖殿的意向有相當的篇幅進行討論。而失去聖殿則意味著神離開塵世,遠離世人與大地,從根本上就改變了人和神的聯系。
基督教的誕生是真正意義上猶太一神論發展的最終結果,因為救世主的降臨意味著等待的終結。但是更進一步的,救世主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預言實現,律法的更新,天地聯合,以及最重要的,唯一神之下的普世大同。但後者也意味著對現有律法的不必然取消以及選民制度的瓦解,而基督教同時伴隨而來的還有神在人身上的實現,這些都引起了猶太人的反彈。
作為對以上二者的回應,猶太人選擇將傳說中摩西從西奈山上獲得的律法書作為聖殿的替代,並將之放到更高的地位,是世界的基礎——但實際上古代智者文學中神創造世界的律法是指自然法則,此處律法書則被神秘化,視作構造世界的神秘法則。同時一些讓人聯想到基督教的要素也被刪去,比如墮落天使的神話或是受難的救世主。但在隨後的神秘主義思想與重大猶太救世主運動中,基督教元素將反復出現,不過這些運動或多或少都被當代經師傳統壓制——這也從側面證明猶太人一直在抵抗的是其內部的自然力量。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諾斯替主義。盡管諾斯替主義主要以基督教形式著名,但其諸多派系傳統是建立在第二聖殿猶太人傳說中的,例如塞特派就以塞特為前驅,這與當時猶太神話內容相近,以塞特為繼承亞當密傳的正義者。而諾斯替中猶太教團的信念和解讀方式就與當時猶太人的神話思想神秘思想相合,喜歡在名字和詞語上大做文章,以提出所謂隱義,甚至一些諾斯替文本提出的神話概念在後期被猶太教反復使用,例如盡頭之海與纏繞諸天之巨龍。在這個時期的猶太教正統派系對此採取沉默態度,任何諾斯替相關的內容都不予記載,此舉使得當時盛行的猶太諾斯替幾乎沒有流傳下來——但它最終並沒有從根本上消滅諾斯替,因為諾斯替和猶太神秘主義乃是同一思想源頭生出的不同支脈。
塔木德的寫作時間跨度很大,最早的片段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最晚的片段則直到公元十四世紀,而塔木德的核心文本則是集中在公元二世紀到公元六世紀寫成的。
塔木德是一套文集,里面收錄了各種經師言論,基本上是對於戒律的執行討論,還包含一些對當時猶太人生活的記載和傳說記錄,里面不可避免的摻雜了大量經師意見。塔木德的出現是為了應對聖殿覆滅後猶太人無法統一的局面而編纂的,但因為此時官方和權威已經隨著聖殿一起毀滅,因此只能收錄當時各種經師據回憶而制定的戒律,導致對同一個戒律的解釋和實踐的描述在不同經師口中差異極大。同時,塔木德里面也收錄了不同經師的神學見解,而這些見解大多屬於智慧文學的延伸。
塔木德有兩個種類,一個是由羅馬帝國下巴勒斯坦地區的經師編纂的,被稱作耶路撒冷塔木德,另一個則是由波斯帝國下巴比倫地區的經師編纂的,被稱作巴比倫塔木德。耶路撒冷塔木德成書時間稍早,但是並不完整,隨著皇帝命令,這些經師離開巴勒斯坦,散布於南歐,東歐與中歐地區。巴比倫塔木德則順利完成,因此影響力最大。
塔木德收錄了相當多的經師見解和神話故事,其中不少故事或寓言有其典型的神秘意味。例如,在一則寓言中提到,神是以十句話(Seferot)創造了這個世界,而在創造以前神先預先創造了十種事物(Devarim),其中包括懺悔,天堂,地獄,祭祀用的小牛,諸如此類。這種對於神創造世界的方式以及內容的寓言式解讀試圖通過分析聖經敘述以對支配世界的法則進行解釋,盡管它本身來自於智慧文學中對於人的美德的抽象褒獎,或是擬人手法來對神進行描述,例如「神以智慧創造了這個精妙的世界」,或是「正義之士是維持世界存續的支柱」。

塔木德同時收錄的還有對於戒律的寓意解讀以及天使的故事,這些也大多是智慧文學影響下理智的濫觴。例如,在解讀為什麼做口舌之罪要殺死一隻鳥然後放飛一隻鳥的時候,經師解讀為,殺死的鳥意味著殺死邪惡的舌頭(Leshon Ra’a),也就是自己說的壞話,而放飛的鳥象徵讓自己說的友善的話能自由生存。天使故事則分三種類型,一種是經師為了表達某種神學觀點而作的寓言,一種是民間習俗和傳說,還有一種是神秘主義者實踐技法時候得出的結論。三者往往是交雜在一起的,寓言中可能包含民俗,民俗可能受技法影響,而技法可能遵循寓言指導。同時因為塔木德對律法的神化,誕生出一批經師傳說,這些飽學經師通曉萬物的法則,因此可以判斷未知之物,甚至行使奇跡。這也為猶太神秘主義在猶太經師內流行預置了溫床。
塔木德同時代的神秘主義流派是有據可循的,並且這些神秘主義圈子的經師在塔木德中留下了許多痕跡,最經典的就是四賢者登天的故事,以及雙經師捏泥人的故事。這兩個故事也代表了兩種主要神秘技法的方向,一種是所謂的戰車升天技法(Maasse Merkava),尋求如同先知厄利亞烏那樣坐著火焰戰車升天,一種是所謂的創世技法(Maasse Bereshit),通過學識解構創世過程,手段以及材料,進行對創世神跡的模仿。這二者往往是我中有你的關系。從塔木德時代開始,神秘主義文本都不再如同偽經那樣追溯先知,而是以塔木德賢者為主角,而這個時代的文本都以經師奈乎尼亞(Nehunya ben haKana),祭司伊斯瑪伊(Ishmael haKohen),經師阿奇瓦(Akiva),以及被放逐的經師厄利耶澤(Eliezer Ben Hyrkanus)為主角。塔木德傳奇中行奇跡者哈尼那(Hanina ben Dosa)與經師梅厄(Meir)雖然以奇跡著稱,但很少有以他們名義寫下的文本,更不談原本存在感薄弱但因為後世託名而名聲大噪的若亥之子西蒙(Simon bar Yohai)。
戰車登天技法留下了非常多的文本,典型如《大宮廷書(Hekhalot Rabba)》。這些書是為指導操練者如何抵達天界而寫成的,並且里面有非常多託名著名經師的論述。按照描述,操練者需要如同民俗中摩西為登山之前作的准備那樣實行齋戒,然後念誦咒語,呼喚天使幫助,然後帶著咒語進入天界。有時候則是召喚天使傳授必要知識然後再帶著這些知識進入天界。天界會有非常多的天使把守關卡,只要遵循天使或是前輩的指導就可安全穿行。最後人就是來到神面前,丈量他的身形——這應該是模仿聖經中厄澤克爾先知丈量聖殿。
盡管這些文本對於天界乃至於神充滿了物質化的描述,比如天界有水和火的大河,或者神的鼻子有五百帕拉桑那麼長,但是依然可以看出文本本身只是借著物質特徵描述非物質的事物。例如神的手臂是一長串的神的名字排列組合而成的字母組——神應該是不會紋身的,就算紋身也不會紋自己的名字——或者有「他的面容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他的面容,他的呼吸是火焰,這個火焰奠定萬物。這火焰應讓你歡喜,因為它就是智慧和奧秘」。這些抽象描述都應令其讀者警覺,意識到自己所閱讀的內容並不是發自物質世界或內心的形象。在這個時代晚期,這些抽象描述也被賦予抽象意義和道德意義,作為智者文學的延伸。
創世技法留下的文本並不多,實際上很多是零碎的小故事。這些故事的一個重要代表就是《經師阿奇瓦的字母表(Otiot de rabbi Akiva)》。這個小故事託名阿奇瓦,因為這位著名經師曾寫下重要的著作《構造之書(Sefer Yetsirah)》,不過真實文本已經失傳。在升天技法中託名他的作品也非常多。這個小故事是目前知道的最老同時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內容是神在創造以前給二十二個字母做答辯,最後選擇以哪個字母作為創造的單詞首字母。這個故事在早期猶太哲學家眼中是一個教授兒童字母表用的寓言故事,但是在另外一些神秘主義者眼中,這個故事是神創造世界前真實發生過的事情,世界就真實按照這些字母的特性而被神所構造。
對於不熟悉這個系統的人而言,要理解這點可能有點困難:為什麼字母和創造世界有關系?雖然創世紀中神用語言創造世界的故事非常著名,但這似乎和字母本身沒有關系。在當時的猶太神秘主義者看來,神用希伯來語創造了世界,因此希伯來語中的元音,輔音以及啞音被賦予了神聖的意義。因為世間萬物都是通過神喚起它在希伯來語中的名字以將之創造,因此希伯來語,就是這個世界的骨架。因為希伯來語里面有五個元音,二十二個字母,因此它們就是神創造世界時構造世界的元素,而世界就是按照語法和詞序排列構造的,一旦改變了一個字母的形狀或位置,那麼一個事物的根本架構就發生了改變。在這神話中,不僅希伯來語被拔高到無與倫比的地位,就連它的語法,詞匯以及發音也無與倫比——盡管如此無與倫比的語言在這個故事寫成的時候早已大幅變形並幾近失傳。
這個時代的護身符和咒語非常獨特,充滿了融合氣息,這是之前和之後的時代都不具備的。不僅它包含了創世技法所提倡的字母神話,也收納融合了其他神話在里面。並且它們的應用也非常廣泛:除了塔木德記載,神秘主義者使用以在操練時保護,也在民間非常流行。這個部分的文本以兩本書為代表,一本是《摩西的利劍(Harba de Moshe)》,另一個是《秘密之書(Sefer ha-razim)》。
前者被發現於埃及開羅,整個文本有非常濃厚的猶太民間色彩,里面內容是一大堆如同猴子打字一樣拼出來的神和天使的名字,然後許諾只要使用了這些名字召喚天使,就可以重復摩西當年使用的奇跡。後者要比前者精妙許多,應該是希臘化猶太人所作。在其中牽涉到七大行星,一周七日,七曜對應的材料,輪班天使的姓名,諸如此類的內容。這些內容在五世紀到七世紀中間出現與當時基督教的崛起密不可分,猶太經師為了同這種新興傳統對抗而默許這種特別的儀式存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應是滿是圖畫的巴比倫咒語碗。
另外,考古發現的民間護身符之中還有更多融合的痕跡,不僅在這些護身符中發現明顯屬於諾斯替主義的護身符,例如伊阿歐神護身符,也發現一些羅馬傳統護身符,基督教護身符和巴比倫傳統護身符,其中赫利俄斯咒語,聖喬治護身符,以及巴比倫咒語碗特別常見,更不必說一些被猶太人沿用至今的閃米特周邊文明的習俗。這充分說明民間實踐永遠不會像是經師記載的那樣與其他教條格格不入,而是更加豐富多彩,妙趣橫生——不少此類護身符更是被經師製成,這使得整個中東—環地中海區域的猶太神秘傳統呈現出此後都罕有的多樣性。

從構造之書到明燈之書:三大學派
構造之書是一卷非常難以界定時間的書,但是因其中包含的大量近東與希臘思想,因此諸多學者將它的寫成年代放到六世紀到七世紀之間。
這部與傳說中阿奇瓦的書同名的作品在歷史上常常被認為和阿奇瓦有關,又因為此書開篇託名亞伯拉罕,說是亞伯拉罕這個神話人物本人得到的這些傳授,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面,猶太人相信這本書是亞伯拉罕本人寫成,阿奇瓦重新修訂後的神秘教導——不過真實情況應該是,在漫長時代中,同一區域的經師借用阿奇瓦的傳說與故事,結合自身的觀念寫下,並隨著理念發展而不斷修改的文本,並託名阿奇瓦為作者。
這本書一開篇就玩了一個文字遊戲:神用三十二條道路雕刻萬物,他以SFR的三種形態創造了這個世界:書本(sefer),數字(sefor),以及故事(sipur),就是十個空間與二十二個字母的轉換,那二十二字母即是三個主字,七個復字以及十二個單字。
這是十個散射(Sefirot,單數Sefirah)第一次正式出現在文本中。可能還存在更早的記錄,但至少在十世紀的時候,人們就認為是這本書最早提出了這套理論。它的詞根,SFR,和文字有關。實際上,散射這個讀法,完全可以對應另一個意思:數字。這也和它的數目形成聯系:通過將十個散射依次排列,這樣,我們就得到一套十進位所必須的全部數字。此處它僅有數字的意思,後來被新柏拉圖主義者賦予了全新的概念,變成今日眾人熟知的散射。散射是猶太神秘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此後的整個猶太神秘主義都是搭建在這上面的。正如其字面意思,這個詞就是散射的意思,在現代希伯來語里面這個詞還被用來指物理中的放射物,取這個詞的原因可能是指散射如同太陽一樣,作為原型向外溢出其對應的德性,而其思想來源應該來自塔木德中神十次顯現自己以創造。
這個文本顯然不滿足於此。在文本中,十個數字被神創造而來,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著一個出現而相連,一個從上一個衍生出來,最後一個又回到神那里,以此形成一個閉合的環。這個描述是這本書獨有的,它是如此大膽以至於後世類似主題的書都沒有這樣的描述。隨後神通過組合自己名字里面三個字母的不同順序,排列組合出了六合。神又將二十二個字母放進來,賦予它們元音,輔音以及啞音,並賦予它們水風火的元素含義,賦予十二周天的含義,等等。於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就出現了。
隨著阿拉伯崛起,波斯帝國覆滅,巴比倫猶太人被阿拉伯人接收。在阿拉伯人半脅迫半交易的政策下,敘利亞和亞述基督徒將希臘語的文本翻譯成阿拉伯文,點燃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求知之火,而猶太人自然跟著阿拉伯人,受益匪淺。從安達盧西亞,突尼西亞,到大馬士革,巴格達,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猶太人都跟隨阿拉伯人學習,將希臘哲學——准確的說,是阿拉伯人接受的神秘色彩濃重的希臘哲學——融入到自己的學說之中,並利用柏拉圖,畢達哥拉斯和亞里士多德的學說為各自的理念而同傳統教法學者論戰,盡管他們接觸到的亞里士多德是新柏拉圖主義下的亞里士多德。此時涌現的故事補遺(Midrash)作為一類偽經和神話文本,將各自學派的理念埋藏其中,散播出去,以支持自身的理念。
這個時期包裝成猶太傳統故事的偽造文本不少是直接抄襲自希臘經典的。例如在這個時期的猶太文學中,神不是將人肋骨取出創造女人,而是創造了一個雌雄同體的原初之人,一面是男,一面是女,不需要其他方式就能自主繁殖,但是被神劈成兩半,變成了亞當夫婦——毫無疑問這是直接抄的柏拉圖會飲篇里面的寓言故事。這些故事的創作目的就是為了支持自身的理論,因此很快這些故事就被捲入論戰中心,並持續影響後世的猶太神秘主義思想。
就在整個環地中海地區的阿拉伯猶太人辯論的熱火朝天時,從義大利和東歐北上的德國猶太人顯得十分安靜。這似乎出人意料,但卻並非不能理解。由於較早就受羅馬帝國影響而搬遷至此,德國猶太人沒有像阿拉伯世界的那些群體一樣直接接受希臘哲學,而是以塔木德研究為核心。他們被稱作虔誠者,相比已經實現阿拉伯化的猶太人,持有古老技法的德國猶太人更貼近他們所在的環境,甚至帶有中世紀天主教的色彩。
這個時期的虔敬者是兼容並蓄的,除了來自巴格達地區的《構造之書》,巴比倫神學家的作品,他們也接受了所處環境帶來的影響——如前所述的天主教神秘主義,甚至還接受了異教,或是一些其他神秘主義,例如德國原生神秘主義,希臘密教和鍊金術。由於這種奇特的包容性——很可能來自於他們本身的無知導致的對於每一種學說都產生的敬畏心,以及對於兩大猶太神秘技法的保留,使得德國猶太神秘主義走上了一條和從西班牙到普羅旺斯地區興盛的卡巴拉傳統所不同的神秘主義道路。高於普通人的戒律標準越過了原本的戒律,成為修行者的必修課,而這原本是不存在於猶太思想的。他們還發展出了懺悔以及補救的方式,像極了當時在天主教內興起的刻苦的告解模式——甚至在此之上還發展出苦修。正如一個虔誠者說的那樣,「聖經預言救世主將為我們的罪惡受苦。我不願其他人為我受苦,因此我為我的罪懲罰自己。」這種苦修主義影響根植於塔木德時期的教父傳說,在天主教影響下誕生,並在後續諸多傳統中出現。
虔誠者不僅繼續實踐升天技法,並且傳聞他們之中甚至出現了先知級的人物。有人曾見證,從雲層中有聲音與虔誠者領袖說話,如同當年摩西一樣。在傳說中,這些虔誠者在天幕的秘密——升天技法中記載的隔絕上界和神座的天幕,刻有萬世的命運,神光從中顯現——和遙感這些特別的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甚至能讓天使和惡靈在使用祈禱詞與神名的情況下遵從要求,這也使得他們影響下出現一些沉迷其中而陷入異端者,「他們為了能獲知遙遠世界的奧秘,就用法術將惡靈的力量附身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就發瘋,失去理智和控制,有時跌倒也沒知覺。當他恢復理智時,就會將他看見的天幕的秘密或是遠方發生的事情告訴他們。」當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說也同樣出現在當時的天主教流行風氣中,中世紀包括聖伯納德在內的聖人就有此類傳說,因此這或是當時猶太人為對抗天主教影響而發明的傳說,但這些內容也作為後世的德系猶太人神秘傳說一部分而融入其文化中。
這個時期的代表是《虔誠者之書(Sefer Hasidim)》。這本幾乎是思想碎片匯集成的書里麵包容了從短篇故事到戒律實踐到修行心得再到神秘色彩濃重的論述,幾乎是一本中世紀德國猶太人生活指南。其中涉及神秘主義的言論非常有趣,因為是語錄體的內容,因此短小卻精煉。例如里面對歷史進行了神秘主義方面的解說,「為了防止猶太人成功召喚天使,巴比倫王進攻耶路撒冷的時候命人塗改了天使的名字」;對鑒別危險的建議,「正如當一個人變形成其他事物——狼,狗,貓,這些動物的時候,他其他地方都改變,唯獨眼睛不變,因此當女巫或惡魔變成其他人物的相貌的時候,他們的眼睛不會改變」;或是對於吸血鬼(Terafim)的描述:
「有些女人被稱作吸血鬼(Estrie),狼人或夢魘雌馬,她們是在黃昏時被創造的。一次一個女人病的很重,就有兩個婦女夜里來照顧她,一個睡著了一個醒著,但她們不知道這個生病的女人是吸血鬼。生病的女人夜間站起,在睡著的女人邊抖動頭發,要飛起來,並要吸血。醒著的女人尖叫著叫醒了她的同伴,她們一起抓住了她,隨後這個生病的女人就昏死了。如果她殺死人並吸血了,她就能存活,但她沒有做到,而吸血鬼需要鮮血,於是她就死了。狼人也是如此。而夢魘雌馬在起飛前必須散開她的頭發,這樣就可以在她起飛前捆住她的頭發,令她未經許可不能去任何地方。如果一個人打了吸血鬼或看了她,她就不能生存,除非她吃了那個打了她的人給的麵包和鹽。同樣,被她襲擊的人也必須吃她給的麵包和鹽,這樣靈魂才能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虔敬者之書中對於此類民間傳說的記載比比皆是,可以相信,這些故事不少來自於斯拉夫和日耳曼當地的傳說。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這個時代還有另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品,《斯拉之子耶穌的字母表(Otidot de Yeshua ben Sira)》。這部小說般的作品因其對於夜之女魔莉莉特(Lilit)的大膽描寫而出名,但其託名作者斯拉之子耶穌唯一真正存留下來的作品是七十賢者本收錄的德訓篇。而稍晚一些的德國猶太人作品,《天使拉孜厄勒之書(Sefer Raziel ha-Malakh)》——一部據稱是天使傳給亞當,亞當傳給諾亞,諾亞傳給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傳給摩西的充滿神學理論的咒語書——則總結並採用了這兩部作品,里面還糅合了已經失傳的技法所遺留下來的片段,包括組合排列字母並與特殊詞根組合以發明天使的名稱。實際上拉孜厄勒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文字遊戲,代表神的後綴放在秘密這個詞的後面,就變成了一個天使名字。

法國普羅旺斯地區的神秘主義學院則沒有他們貧窮的遠房親戚那麼拘束並固守成見。他們擁抱希臘哲學,並以柏拉圖主義思考神和萬事萬物。由於是從義大利遷到法國,又因為法國聖路易的政策而離開法國,最後得到羅馬教廷特別照顧而在羅馬直轄的普羅旺斯地區建立社群的猶太人,這個族群比起另外一批遷徙到西班牙的猶太人,更接近義大利傳統。
普羅旺斯學院是拉瓦德家族主持的。第三任拉瓦德明確將散射(Sefirot)引入猶太神學的討論核心,隨後,他天生瞎眼的兒子,新柏拉圖主義者盲人伊察克(Yitsahk Saginaor)則提出了無盡(Ain Sof),並在他的學徒阿孜厄勒(Azriel)等的幫助下收集材料,在構造之書的基礎上編纂了卡巴拉(Kabbalah)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明燈之書(Sefer Bahir)》。他的弟子則通過組合散射和無盡,將諾斯替與散射結合,發明了如今人盡皆知的生命之樹模型(Ets Hayim)。由此,被人以卡巴拉之名熟知的猶太神秘主義於普羅旺斯誕生,而這種神秘主義也大言不慚地冠上了卡巴拉一名:卡巴拉意思是接受,暗示這套理論是從亞伯拉罕甚至亞當處獲得的唯一真實的傳承。
明燈之書是完全由一些未知來源的前人作品拼湊在一起的,或許有些片段可追溯至阿拉伯崛起以前,而該文本中也夾雜了盲人伊察克和他弟子阿孜厄勒的論述,因此整個文本支離破碎,和語錄體的虔誠者之書完全不是一種風格。這部作品背叛了,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創世與升天技法留下的神話結構,尤其是升天技法中從阿納飛厄勒到亞歐厄勒的十重聖名天使建構的天階體系,另外選取了新的神話模式,盡管作者本身可能並不是故意的。盡管如此,這本書依然是卡巴拉的第一個正式文本,並且是要了解卡巴拉就必須閱讀的書。
太初,一切不存在——這是一個典型的新柏拉圖式敘述——然後,無盡(Ain Sof)從冠冕(Keter)中以智慧(Hokhma)打開天地。無盡是一個典型的新柏拉圖主義的觀念,一個不可言說無法理解的,甚至連宗教意義的神都稱不上的,連一個東西都不是的東西。智慧開創世界,為了論證這點,明燈之書曲解了聖經的智慧書中「神以智慧創造天地」一句,將抽象理念曲解為實體,以維護自身。隨後,從智慧中生出理智(Bina),理解和智慧構成了一個隱藏的領域,就是知識(Da『at)。冠冕,智慧和理解,是天意決斷,不可違逆,因此這三者組成一個大三角,和下界隔絕。隨後,從理解中生出六界,構成世界的六極,也就是六個散射:慈悲(Hesed),力量(Gevura),憐憫(Rahamin),威嚴(Hod),永恆(Netsah),基礎(Yesod)。這六個散射挪用自厄澤克爾先知書中對神的贊美,後者稱神擁有以上六個德性,而此處就成為神的六個肢體。最後從基礎中生出寶座,或者說王國(Malkhut),就是這個世界,或是承托神聖奧秘的猶太人。因為猶太人生來是為了承托奧秘的,如果早夭便無法承托,因此明燈之書認為這些早夭的靈魂會經歷轉世(Guilgoul)以實現其使命——這些諾斯替敘述無疑受到了當時南法興盛的基督教卡特里異端的影響。
毫無懸念,此文本中大量的神秘主義意向同諾斯替是如此接近,自然,對此文本的思想來源的猜想中有相當多都指向諾斯替主義。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散射理論,這個理論讓人不由自主的想起敘利亞諾斯替中發展出的普累若麻(Pleroma)。普累若麻是希臘語完美的意思,在諾斯替主義中是神的發散。在諾斯替神話中不可認識的神通過思維運作同時生發出他的心靈和他的形象,作為第一組普累若麻大三角,再依次衍生出剩下的普累若麻,然後再以此完成世界的構造。這種運作模式也同樣存在於散射之中。除此之外,對於語言語音的過分強調以及對於世界元素的衍生順序,也將二者組合在一起。
諾斯替可能確實對猶太神秘主義造成影響,尤其是塔木德時代的美索不達米亞有大量被稱作正直人(Hanif)的諾斯替主義者,這群活躍的諾斯替主義者對後世的阿拉伯產生有巨大的影響——又因為他們也遵從亞伯拉罕神話,是故比波斯人更能影響到當時的猶太人。不過猶太學者大多不認為猶太神秘主義是諾斯替的影響,認為這是猶太文化自己生成的。Gershom本人即論證說,諾斯替中普累若麻是描述的宇宙生成,而散射則針對宇宙秩序。這話確實不錯,但是散射的初生也是描述的生成,進而成為秩序。散射沒有秩序與生成間的對立,一切都是創世時那樣完滿,而不似諾斯替那樣在生成與現有秩序間劃下一道鴻溝——這顯然迴避了惡和人的墮落的問題。不過塔木德時代就有經師反對將惡放在神所不管轄的范圍內,認為惡也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以此實現內部消耗惡的問題。但這一論調並沒有實現提出此論者想要的穩定,因為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惡與秩序的分離將越來越明顯。
不過對十個散射進行進一步探討前,此處必須承認,散射,或者說普累若麻類型的模型早在塔木德時代就有隱約論述,而Gershom認為這是猶太人中的諾斯替主義者留下的。正如前文所述,塔木德中有這樣一段話:「世界是在十個基礎上建立的:智慧,理解,知識,力量,喜悅,權力,正義,公道,愛,憐憫。」這里可以看到,後世的經典散射組合中已經有幾個散射特質出現在這段話里面。盡管這句話有深刻的象徵意義以及道德主義傾向,但是它的神秘主義特質也不容忽視,尤其是涉及抽象屬性的世界支柱以及對代表完美的數字十的追求。
由於這十個散射被普羅旺斯學院用來解釋聖經中涉及神的官能,因此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混亂:明明散射是神的人物造型的不同部位的器官,比如頭和手腳,但它又同時是聖經里面說的「神從天上張開的手」上的十個手指。也因此,摩西舉手幫助希伯來人,就成為通過伸出手指這種方式,和無形的邪惡力量對戰。創世與升天技法遺留下來的文本被用十個散射解釋,其結論與原始文本大相逕庭,讓人非常懷疑詮釋者是否了解該傳統。同時,對於這十個散射的描述,明燈之書將之附會到厄澤克爾先知看見的形象,而一開始原本應該解讀為天使顯現所帶來的火焰和風暴,則被解讀為試圖抵觸散射的邪惡力量——這是盲人伊察克為惡找到的一個位置,以解釋構造之書出現的天界大龍。而正是他此處蹩腳的解讀,為卡巴拉解釋惡存在這個問題奠定基礎。

阿孜厄勒將他所學帶回西班牙,開創安達盧西亞學派,該學派為卡巴拉奠定了很重要的傳統,對於已有文本和儀式的神秘化就是這個階段完成的。例如大祭司的祝福,其手勢被卡巴拉稱作完滿之流(Shefa Tal),通過兩個手組合做出字母Shin的形狀,代表全能者(El Shaddai)一名,又有二十八個指關節,構成力量(Koah)一詞的等價數字,每個關節各有對應的神名字母,最後兩個掌根重合代表天地交泰,構成神的四字之名。此類對聖殿時期傳統充滿想像的神秘詮釋遍地都是。
但安達盧西亞學派最重要的人物則是阿孜厄勒培養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弟子:納赫瑪尼德(Nahmanide)。納赫瑪尼德沒有留下非常著名或決定性的卡巴拉著作,他對他老師傳授的卡巴拉的使用都體現在他對聖經的註解上,他也是當時猶太哲學,經典學術以及神秘主義學說的集大成者,從他以後猶太神秘主義與經典被有效捆綁在一起,並且成為聖經真義,而正是這種註解為後世卡巴拉主義者隨意使用聖經打開了大門。他發展了塔木德以後對律法的神秘化詮釋,大大拓寬了律法的內容並成功通過這種方式激發人心中遵循律法的熱情。同時,他的教導流行於他所在的那個時代,他還曾為他的偶像邁蒙尼德(Maimonide)四處奔走,並出席西班牙猶太—基督教辯論,維護猶太人的理論。如果沒有他的這些工作,那麼後面的卡巴拉成果就不可能出現。在他看來,自然是超越奇跡的,而奇跡並不存在,因為神從不干涉它定下的自然規律,因此奇跡不過是神在創造世界時預設的特別法則,僅出現在特定的時空節點——這種詮釋方法來自他的偶像邁蒙尼德,也導致後世卡巴拉學說將早期神秘主義期待的奇跡之神放置於卡巴拉關注的自然之神的下方,而最上方則是哲學家之神,也就是邁蒙尼德的神。
他詮釋聖經的方式非常獨特而具有神秘色彩。在他看來,聖經是創造世界的藍圖,因此聖經之中就包含所有的自然法則和天意,不過後者是以秘密的方式隱藏了起來。因此,他主張聖經的每一個字母都是特別而有神秘含義的,整部聖經是神的密名,而找到並予以解讀就是他的職責。例如,他是這麼註解十誡的第四條的:「你應孝敬父母。這里的父母指的不單純是肉身的父母,更是你靈性的父母。他們就是書面律法和口傳律法。書面律法是父,如果沒有口傳律法,書面律法就晦澀難解,條律不完整,無法實踐;口傳律法是母,如果沒有書面律法,那麼口傳律法無所依,什麼也無法生成,無法指引。當二者結合時,就化作天上的泉眼,神的水源源不斷通過二者的結合湧出。」傳說中他的弟子反對他的言論,認為聖經里的一句話不可能有所有猶太人的名字憤而出走,最後他通過一種神秘的詮釋方式解釋了這句話,使得該弟子悔改——不過是因為該句有希伯來字母表里所有字母,因此他通過指出里麵包括這些字母並拼出該弟子名字的縮寫以證明自己的觀點。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猶太神秘主義者,他是如此的與眾不同,以至於在歷史上很長時間,他都是沉默乃至於被除名的。他就是西班牙地區稍早一些的學者阿維茨布隆(Avicebron)。可能受他身邊的阿拉伯學者影響,他不屬於卡巴拉也不屬於虔敬者,他的思想反而接近早已消亡的新柏拉圖密教,而他就是一名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他的作品被翻譯介紹到拉丁世界,當時經院哲學界的柏拉圖主義者為他驚嘆,並以他的《生命泉(Fons Vitae)》為圭臬——因此阿奎那曾在他編寫的索邦哲學課教案上狠狠批判過他。
阿維茨布隆在猶太世界只保留了幾首詩歌,除此之外他其他作品沒有保留,並且直到幾乎一千年後,猶太世界才重新通過基督教世界認識了他。他在當時的猶太世界處於被排擠的狀態,各個猶太社區都禁止他的作品,也拒絕他參與。但從書信來看,當時熱火朝天的卡巴拉學者——他們基本上都是猶太社區領袖和立法者——私下都在談論他和他的作品,並且他的思想可能因此進入了卡巴拉最重要的典籍中。假如沒有他,那麼今日的卡巴拉就會是另一種樣子了。同樣受到排擠和爭議的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猶太哲學家,被同為亞里士多德派的阿奎那贊賞的邁蒙尼德。只是邁蒙尼德借著民族主義的西風翻身成為比摩西更偉大的摩西,而阿維茨布隆卻在他的同胞中沒有這個運氣。
邁蒙尼德,阿布拉非亞,以及光輝之書
邁蒙尼德不是重要的卡巴拉學者,他對神秘主義學說的貢獻並不是最突出的,但是因其極其特別的地位以及與後世重要文本的聯系,以至於在論述猶太神秘主義歷史時不得不提。盡管他今日被認為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但是他學習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是從阿拉伯學者的著作中來的,而這些著作實際上有許多是建立在敘利亞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者的詮釋和託名之作上的,也因此他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有深刻的新柏拉圖主義的特徵——這個問題直到拉丁翻譯運動以後被大阿爾伯特及其弟子阿奎納發現,不過邁蒙尼德的這個印記也導致後世卡巴拉學說發生轉向。
邁蒙尼德原名邁蒙之子摩西,邁蒙尼德是他的尊號。他是一個亞里士多德派西班牙猶太人哲學家,與第三代拉瓦德同一個時期,比盲人伊察克更早。據信早年他通過偽裝成阿拉伯人的模樣跟隨阿拉伯學者學習,曾大量挪用波斯蘇菲學者安薩里(Al-Ghazali),敘利亞阿拉伯學者法拉比(Al-Farabi)和西班牙阿拉伯學者阿維洛伊(Averroes)的學說,後來又作為薩拉丁(Saladin)的醫生和顧問參與對抗十字軍的戰爭。這個學者在其青年時期曾對律法實踐感到疑惑,因為當時來自各個地區的猶太人混雜,儀式和習俗不能統一。為此他向巴格達的學院院長(Gaon)寫信,這些學院院長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充當猶太律法最終解釋人與裁決者,整個猶太世界每天都有無數人寫信給他。但院長在百忙之中的親筆回信並不能解答他的疑惑,這個年輕人決意打破學院派對塔木德的壟斷,自主編寫一部大一統的法典和聖經註解。
這種莽撞沖動的行事方式無疑在當時是對傳統的威脅。從第二聖殿毀滅以降,猶太律法就並不統一,全部都是遵循各自師承與地方習俗進行的,即使是對聖經的解讀和對法典的詮釋。但這個青年人離經叛道的行為還不止於此,他對律法和聖經的大一統解讀中夾雜大量私人意見,創造理論,甚至他還巧立名目為自己違反規定辯解。
例如,他對聖經中含義模糊的先知書以他提倡的理性主義思維解讀,最後得到一個偽科學的結論:在他看來,先知看見的各種形象其實都是符號和比喻,描述的不是神,而是一種「已經過時的天文學結論」,「認為天上是四大行星」——即使他提出的「圍繞地球轉動的七大行星」這一指正方案在今天看來也是過時的——並且因為當時民眾愚昧不能懂所以用這種方式書寫,現在人們有真實的知識自然可以解讀;又有公開發表他寫給其他人的書信這種方式,將他自己理解的升天技法真實知識傳播出去——原本這是一種必須一對一,嚴重依賴學徒領悟力和感知力的神秘主義教學,但在他的解說下,一種基於論斷而非經驗的個人見解變成大眾心中的真實見解;他認為先知從猶太世界消失的很大一個原因是猶太人開始變得悲觀並易於感傷,只有狂喜才能讓先知的靈氣駐於人身上,而悲傷和畏懼等情感要素只會趕走神靈;人作為神的形象在於擁有理性,可以思考事物,因此令人永生者無他,不過是對神的知識,因為神就是神的知識,通過神的知識人的認識得以與之同化;他遵循阿拉伯亞里士多德學派的觀念,否認創世和末日,否認肉身復活,主張永恆的復活僅僅屬於擁有正確靈知的人的知識靈魂,而不是作為人的生者的靈魂,因為唯獨靈魂中接受了靈知的理智部分才能永存;他還隱晦的批評聖經作者愚昧無知,看不出巫術之流原本是胡說八道。
毫無疑問,這些激進的思想引發了強烈反彈,分化人群。傳統學者抵制他的作品,禁止學院傳播他的書,盲者伊察克的父親,第三任拉瓦德甚至親自寫書反擊邁蒙尼德,而維新派則分發討論他的作品,將他視作先知。
就在兩方的鬥爭趨於白熱化之際,一個決定性的事件發生了。身處西班牙的邁蒙尼德反對者不敵支持者的壓力,於是將邁蒙尼德在其書中反對基督教的文章舉報給羅馬當局,試圖以此打擊邁蒙尼德支持者。羅馬當局的審查者經過審查後發現確有其事,於是下令搜繳並集中銷毀猶太社區的邁蒙尼德文集。這件事引起了猶太人的極大反彈,尤其是因為前段時間在兩派猶太學院競爭下的告密導致基督教世界集中銷毀塔木德文本這一事件引起了猶太人恐慌。基督教世界反對邁蒙尼德的消息立刻傳遍了整個猶太人世界,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盟友的態度,猶太人一邊倒的支持邁蒙尼德。自此邁蒙尼德被捧上神壇,甚至與立法者摩西並立:「從立法者摩西到邁蒙之子摩西(邁蒙尼德),沒有人能超越」,甚至進一步解釋說,「立法者摩西將律法從天上帶給我們,而邁蒙之子摩西則解釋了律法,讓我們知道律法究竟在說什麼。」這夸張的描述無疑有貶損立法者摩西的嫌疑。自此,邁蒙尼德以後,聖殿相關的一切被禁止討論,後世只能復述前人的思想,而後世所有猶太人,尤其是卡巴拉教團,都將邁蒙尼德的著作抬高到第二聖典的地位。
邁蒙尼德的思想席捲整個地中海猶太社區,而影響最大的自然是安達盧西亞猶太人。他的作品在西班牙廣為傳閱,而他對猶太思想的破壞性建設也隨著傳播而蔓延。所有理論中首當其沖的是他對於神的詮釋。在他看來,神只能以否定的形式說明,人不能說神是什麼,只能說他不是什麼。這種新柏拉圖主義色彩鮮明的否定神學並不孤獨,除了之前提到的普羅旺斯學院以外,在基督教的偽迪奧尼修斯處也有回應。但他接下來提到,因此神不可能有人性和人格,神不對任何事物予以肯定,甚至這個不可名狀的存在者就不是神,連存在者也不是:因為人不能對神予以任何形式的肯定描述。既然神不會是我們所能知或想像的,因此聖經和塔木德里面會同人一起喜怒哀樂,聆聽人痛苦或與人分享喜悅的神並不是真的。哲學家應當知道真神什麼都不是,而非哲學家則需要相信聖經所描述的會喜怒哀樂的神,因為對於非哲學家這類沒有靈知的人,相信這樣的神有助於社會穩定。
邁蒙尼德代表的理智至上主義得到了自塔木德時代以來在猶太人中就存在的理性至上信條崇信者的追捧,他對神的描述也成為卡巴拉的核心理念。自此卡巴拉的神被很明顯的分為三個部分:最外圍不可認識的哲學家的神,處於中間的自然法則的神,以及最低級的創造奇跡的神——這種劃分要部分歸功於邁蒙尼德及其背後的理性至上信條,他們相信奇跡是在特殊情況下生效的自然法則造成的,因此他們從根本上否認了神跡。邁蒙尼德也討論過神秘主義的知識,例如在他的知識論中就討論過天使階級的問題,他還將戰車升天手稿斥責為無意義的迷信。但無論如何,他的思想被後人用於討論所謂神秘主義,這應該也是他沒想到過的。

在冊法特教團出現之前,一個特別的猶太人突然跳入猶太神秘主義歷史的舞台,他便是亞伯拉罕阿布拉非亞(Abraham Abulafia)。他曾游歷以色列,並到達阿卡(Akka),或許曾經拜見了該地的邁蒙尼德家族——此時邁蒙尼德的孫子在將阿拉伯人的蘇菲主義引入猶太人之中,這種嘗試如同他祖父曾經做的那樣——並最終在哲學家指導下研究邁蒙尼德的作品。後來他又返回西班牙,在那里研究德國虔敬者領袖對於構造之書的註解。
隨後他自稱救世主——這正是當時的救世主運動潮流,卡巴拉出現後幾乎所有重要的猶太神秘主義者都以救世主自稱——並要讓羅馬主教皈依。按照他所說,當羅馬主教聽說他來了以後,便揚言要把這個狂妄的騙子抓起來,並在大門邊立起了火刑柱。阿布拉非亞自稱曾經進入宮廷並完好無損的出來了——當然,也可能他根本就沒去。不過在他到來前,這個羅馬主教因為心髒病發而去世了。阿布拉非亞後來被發現並被投入監獄,沒多久又釋放了。他一直以救世主自居,寫了不少作品,但是受到西班牙卡巴拉學院抨擊,直到他去世為止。
阿布拉非亞主張字母推演法,這歸功於他對於神之名號的鑽研,而此啟發來自於德國虔敬者。阿布拉非亞同菲奧拉的若雅敬(Joakhim of Fiora)的追隨者關系緊密,他主張世界分為三個時代,而他們即將面臨最後的時代。他將梅塔特隆視作是先知書中坐寶座者,他身上有十個散射的分配,而他的影子,或者說他的另一面,則是桑達勒風(Sandalfon),他的高度從大地直到天空,但卻是黑暗。這個世界就是這二者的交戰,桑達勒風代表惡,誕生於梅塔特隆,但它卻以為它在反抗梅塔特隆,它的化身是黑暗大蛇Tal,纏繞天空,由字母和名字束縛人類的肉身和靈魂——一個典型的諾斯替因素——而它的人間化身是耶穌。相對的則是以色列,梅塔特隆的化身,他們的職責是淨化創造,而他將作為救世主完成對耶穌的清洗。這種古怪的描述加上他對於神名的玩弄——YH是梅塔特隆,誕生了VH桑達勒風,梅塔特隆又是完整的整個YHVH——與後世卡巴拉比較,可以明顯看到他對於光輝之書代表的卡巴拉系統的影響。
阿布拉非亞對神的名字進行了許多創造性的闡述。他解釋說,神的名字萬軍之主,代表他是一切字符的主人,這里的萬軍是指一切字符和詞句,因此這使得這個名號代表了神明主宰一切的性質。他認為因為神以希伯來語說話,所以一切語言來自於希伯來語,但這潛在的證明裂分與誤解存在,這同樣出現在猶太人和外人中,而猶太人中的諸多言辭只是在加深人對神的困惑——這個批評借自天主教。根據他對於散射的掌握,他將神之體的構造描述為三位一體的形式,第一個散射是神明的精神,第二個則是父,因為是數字上的AB,對應神名中的YH,而剩餘散射組成一個整體,被稱作是子,受YH所生發,對應VH。他將第一位稱作神聖精神,第一引導者,是因為它是智慧,因此統治王國,所以擁有冠冕,而獲得這種真知者具有王之權威,可以七十種語言宣說。因為這種生發特性,他認為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煉丹爐,萬物在其中以神聖法則為火焰煉化,而語言因其過去未來三世特性而是三位一體,因此是冶煉的主體。這種煉化是通過對字母進行調配實現的,按照他的說法,這被稱作永無止盡的劍,這種對文字的運用本質上是在進行淬煉,使得精神走向神聖的智慧,這也就是對律法的參悟。這種上升過程將會受到來自神聖的試煉,就是梅塔特隆本身,每一層都需要通過檢驗——這里他玩了一個文字遊戲,將撒殫一詞與神聖之靈等同,並暗示說這種試煉是由神聖之靈進行的。因此這里必須將所謂的惡和神聖統一,因為它並非邪惡,但只有將它們分離才會誕生真正的邪惡,也就是龍,不過這也意味著真正的邪惡本身是具有缺陷的,因為它與其根源分離。這些都發生在心靈之中,因此正確的裁決非常重要,而只有神聖律法的智慧足以勝任。在這個對神聖智慧的參悟過程中,操作者必須審慎進行,而通過這種參悟,神聖智慧,試煉對象與操作者三者結合,也就是記憶,認識和知識結合,操作者的自我認同將會與天上的裁決者合一,在這個過程中其自我認同被梅塔特隆所取代,因此神聖名號的判別就非常重要,在他的觀念中這成為制勝邪魔的法寶——這即是聖法重述,也就是創世重現。這些內容對後來的光輝之書神話有巨大影響,而它們出自蘇菲主義。
由於阿布拉非亞觀念中的普世性,這個自詡為救世主的狂人在不貶損希伯來語的傳統地位的情況下賦予其他語言以肯定,甚至發出感嘆,將理解他的教導的外人稱作未經教導的真正的聖民,而拒絕他的猶太人則不是——這番言論似乎削弱了猶太選民論。而他的作品雖然受到後世卡巴拉信徒的稱贊,但卻大多沒被出版,可能因為阿布拉非亞的教導完全無需猶太選民的身份就可學會,有削弱選民特權的嫌疑。與之相對的,在西班牙卡巴拉群體中誕生的卡巴拉最重要的典籍,不僅加強了猶太選民論,甚至更進一步取消了阿布拉非亞的實踐類型的合法性——阿布拉非亞雖然反對魔法, 但是他的字母實踐還是被很多人當作魔法之用,而且他的弟子就神秘操作並不避諱,這是禁止的理由之一——不過這部典籍自己也沒有逃過被用作魔法實踐的宿命。這部書就是大名鼎鼎的《光輝之書(Sefer Zohar)》。

光輝之書是卡巴拉最重要的典籍,一些卡巴拉信徒在提到它時會稱它為神聖的光輝之書。這部書被譽為是比聖經和塔木德更傑出的啟示,甚至有言論認為,聖經的啟示只是啟示的皮毛,而光輝之書則是啟示的靈魂和內核——盡管整部書是想像中的一世紀賢者在想像中的巴勒斯坦進行旅行和教學的小說式偽經。這部書中提及的一些經師根本不存在,書中的巴勒斯坦地理描述也有很大的問題。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很簡單:這部書的作者根本沒有生在一世紀或稍後的一兩個世紀內,也對巴勒斯坦的土地幾乎一無所知。
毫無疑問,在書中反復出現的塔木德人物名字是作者為了讓他的讀者將此書與塔木德聯系起來的重要手段,但這些人物都和塔木德所指的那些人物相差太遠了,尤其是人物關系和時代這方面,以至於它並不能真的遮住讀者的眼睛。在這部書出現的那個時代,就有經師在書信中提出對於這部書的質疑——一個名叫萊昂的摩西(Moshe de Leon)的人大肆推銷這本書,而在他以前,這本書不為人所知。
早在西班牙學派還存在的時候,懷疑的矛頭就指向這個摩西,認為他才是光輝之書的真實作者,而研究結果並沒讓人失望。今天幾乎可以肯定,即使這個摩西不是所有作品的作者——顯然他也不是——至少也是主要內容的作者。萊昂的摩西的作品和光輝之書的比較研究持續了很長時間,而其中有不少內容——筆法,措辭,尤其是思想——是異常接近的,並且光輝之書與明燈之書的聯系也十分明確,尤其是明燈之書里面才出現的虛構人物在光輝之書里面也出現了。
另外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則是邁蒙尼德。邁蒙尼德的思想可以說是整部光輝之書最重要的思想來源,這尤其體現在他對於神的描述這方面,因為這部分反復出現。正如邁蒙尼德拒絕將聖經神話的神稱作真神,這個作者也一樣,不過他還是很謹慎的借用了其他卡巴拉作者的作品——不過是以含糊其辭的方式表現的。這位作者將散射稱作是神的真相——讓人想起明燈之書的說法——神的各種名字各種字母指代生命之樹的不同部分。莉莉特是亞當妻子這個晚期德國猶太人發明的驚世駭俗的說法被收錄。波斯蘇菲行者安薩里的影子隱約可見,除此之外還有深刻的阿維羅伊的印記,可能是跟隨邁蒙尼德一起進來的;另外還有一些隱晦的新柏拉圖主義的表達,這些表達有嘗試統合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痕跡,可以肯定這是受到阿維茨布隆的作品的影響。
但除了這些猶太社區內部的特徵外,一些來自文化外的特徵也足以引起人的注意。比如人物場景和故事進展的描述非常詳細冗長,這不是如同塔木德中對於真實情況的回憶和記錄,倒讓人想起中世紀西班牙基督徒中興起的神秘劇——在這種公共表演中,演員的聲音無法被遠處的觀眾聽見,因此演員以夸張的動作和對象徵器物的關注以達到解釋效果。在光輝之書中出現的智者Sava與其兒子天才Yanuka的故事則是變形的耶穌與天父的故事,尤其Yanuka為了以色列而自我犧牲。書中對猶太祖先在荒野中修行的描述,這種行為並不是真正的早期猶太修道士所實踐的方法——這種修行早已失傳並且不可能為他所知,而且這里修行的描述有很明顯的來自北非和阿拉伯的蘇菲行者的影子。光輝之書中對原初之人Adam Kadmon的贊嘆,對字母之海的延伸性描述,靈魂之根和四重世界的論述,都毫無疑問看見來自安達盧西亞蘇菲的影子。這也並非不能理解,阿方索十世時期的西班牙王國處於和平之中,猶太人雖然受到溫和對待,但外界思想的侵入對猶太人身份造成威脅,而光輝之書則是對這些外來思想的回應——更加典型的例子是,在卡巴拉於巴勒斯坦和埃及爆發式傳播之前,當地的精神核心是一種被稱作猶太人的蘇菲的神秘主義哲學。
整個光輝之書對聖經進行了解構,並像是粘貼剪報一樣將聖經和塔木德的片段按照作者需要任意裁剪,從段落的引述到某個單詞的某個字母的特殊寫法——比如某個字母的某一筆寫的比平常要短一點——都是光輝之書盡情發揮的材料。模仿天主教對聖經的四相解讀,光輝之書繼承了納赫瑪尼德的解讀法,將聖經區分為字面,數字,字音,以及秘義的四重意思——前面三重幾乎是廢話,只有第四重是光輝之書需要的。在光輝之書的描述下,聖經是一個活動的生命體,整部摩西五經是一個大寫的神之名,而里面每一個字都是神的呼吸。當猶太人解讀的時候,就是神的生命進入活躍階段,因此托拉的每一個字都有密意,每個解讀都和當事人相關。當然,在這個層面上的時候,聖經本身在說什麼已經不重要了,光輝之書如此評價說,「聖經實在是寫的很差勁,若非其中的密意,我們完全可以重新寫一部比聖經更好的書。」——此種對於經典的批判,幾乎是邁蒙尼德思想的延伸。
光輝之書對於原生的猶太神秘主義也進行了顛覆,後者的代表就是最初期的升天與創世技法。在光輝之書的作者看來,這些技法是「二流的」,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透露更隱秘的,從亞當直到摩西所傳的獨屬於光輝之書的秘密——即使光輝之書的作者對這些已經失傳的古老技法一無所知也不妨礙。在升天和創世技法中所探討的,是處於下界的人走向天使和神的王座的深奧旅行。但光輝之書並不止步於此,它要進一步討論更深奧的事物,也就是寶座上的神。在光輝之書的作者看來,這個寶座上的神是更內在,隱秘的世界,是神的一種顯現——換言之,它就是生命樹,是十個散射。
這十個散射被認為組成一個人物圖像,也就是坐在寶座上的神的形象:也就是說,先知看見的坐在寶座上的神不是一個神,而是這十個散射,神創造世界的代表。阿孜厄勒將其排列成樹以後,看上去就更像人的造型了,而光輝之書的作者直接採用了這個造型,作為他的理論模板——但顯然,在此處,原本的抽象概念變成了實體,而關系圖也變成了一種穩定結構。整個散射是神的創造的涌動,是神遞進的對自身的宣說,換言之,啟示就是創造,創造就是啟示。
光輝之書覆寫過的創世神話是如此展開的:在萬有和虛空都不存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原點。這個原點是無形的,但從中湧出一切。這個原點就是無和存在的交界處,是無之神從沉寂中活動的行為。在此之先,神不存在,只有空無(Ain)。這個原點,就是智慧(Hokhma),它向外表述,就成為了理智(Binah)。理智從中生出七個分流,變成了下界的七個散射。這就是散射的創生過程,也就是世界的創生過程。這些散射組成一個整體,貫穿始終諸界,世界是它的發展,它則是構成並維持世界的主幹。它們是神的德性,神的名稱,而神的創生之力在其中涌動。在下界,它有一個對應,那就是人。
光輝之書運用文字遊戲,將抽象的理論以一種原始的方式進行表示。上界的誰(Mi)——光輝之書中,誰這個字所指代的那個散射就是創生的源泉之一——對應下界的什麼(Ma),而上下界也分為這里(Ze)和那里(Eleh)。這本質上區分的其實是主客體,認識者和被認識者。而認識者和被認識者再度的聯合則是神(Elohim),在這里由作為認識者的誰(Mi)和作為對象的那里(Eleh)組成的主客體再度一致。因此光輝之書對創世紀第一句話進行了顛覆語法和含義的解讀,原句為:太初,神創造萬物(Bereshit bara Elohim),其中神這個作為行動發出者的名詞放在創造這個動詞後面,這是在聖經希伯來語中幾乎隨處可見的語法形式。光輝之書顛覆性地將之解讀為:在原點(Reshit在光輝之書中是原點)創造(bara)神(Elohim)。神變成了被創造的,創造它的是原點,而原點是空無所生。
因為這種主客體的分別和統一,光輝之書發展出一對特別的思想。首先是神所代表的完美秩序世界,和與之分裂的下級世界,二者之間存在鴻溝——這讓人再度想起瓦倫廷諾斯替中三十三普累若麻,但是還沒完——上級世界是由十個散射構造的,和下級世界不同,下級以形象顯現的世界則是從散射中分離出去的。與下級世界一起分離的,還有第十散射,神之存在(Shekhina),一種女性形式的世界表述。它在世間流亡,而它其實還有另一半留在上級,在基礎(Yesod)之中,為神所保留,是未經過玷污,沒有被邪惡盤踞的——瓦倫廷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就給出過精妙的原型,上級的索菲亞和下級的索菲亞分離,下級的索菲亞被掌權者所捕獲,在世間流亡:而這個教導最初的來源是新約中和耶穌弟子作對的魔法師西蒙。
隨後存在的典型思想,則是世界的統一性。萬物都為神的光芒所涵蓋,雖然秩序之鏈存在於遞進的諸世界之中,但是它們是相互聯系的,整體的,萬物因此聯系在一起。整個世界,神和人,是一同脈動的,世界最內在的涌動,發散為最外層的活動。神通過波動這種方式源源不斷進行創造,以維持世界及萬物存續。由此,神的本質既存在於上,也存在於下,既存在於內,也存在於外。通過這種方式,光輝之書將聖經中描述神的光輝充滿天地解釋為神的光,或者說神的力量,內在的存在於上下,萬物形成一個整體。
除卻阿布拉非亞的敘述——Gershom在他的書里面提到萊昂的摩西和阿布拉非亞的弟子相互影響——邁蒙尼德的敘述也在其中有相當的力度。非猶太的來源,則可以看到阿維洛伊的影子,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的九章集中的學說——據說萊昂的摩西學習過這部被誤認為是亞里士多德所作的作品,也可能前二者也是跟隨邁蒙尼德的思想一起進入光輝之書的——以及蘇菲式的結論,例如伊本阿拉比(ibn Arabi),一個年代更早的西班牙蘇菲賢者提出的神我同一的理論,就和此處描述幾乎一致。
最後值得一提的則是這部書中對於惡以及抵抗惡的描述。在光輝之書中,惡是從神本身流露出來的,是神的另一面——或者說是神的顯現(Shekhina)的另一面,不過在光輝之書中,神的顯現就是神,惡不過是她行使破壞的黑暗女神之貌。惡是如此出現的:太初,黑暗天使撒瑪厄勒(Samael)是生命之樹左端代表神之憤怒的支柱的一個天使,太初時憤怒之柱與右端的慈悲之柱沒有保持平衡,憤怒之柱的力量聚集下移,並催生了混沌的黑暗力量,這股力量就被撒瑪厄勒主導,成為他的仆從。黑暗力量上移並裹覆世界,也就是最下級的散射,王國。因此,神之顯現被撒瑪厄勒控制,在世界流亡。而在太初的時候,神為了阻止如此局面發生,於是擊穿了撒瑪厄勒與莉莉特結合所生的黑暗巨龍的顎,讓光芒得以穿過並進入被它包裹的世界。而這個物質世界,就是墮落的結果,令人從以太身體變成了肉身。
由於這個世界被黑暗包裹,於是神不斷往世界中注入力量,將神聖的火花落入世界,以從內部解除惡的控制。這些火花就是神創造的唯一而真正的人類以色列——或者說猶太人,其他人是黑暗仿照真人創造的——他們就是神的顯現(Shekhina),他們的流亡就是神的力量被黑暗追逐而帶來的流亡。這個世界滿是對於神的顯現的迫害,這是因為神的顯現無時不刻不受到惡的掠奪,黑暗需要神的力量供給同時又仇視神的力量。猶太人通過祈禱這種方式,激發新郎與新娘,也就是憐憫(Rahamin)與王座(Malkhut)交合,進一步引誘父和母,也就是智慧(Hokhma)與理智(Bina)交合,上升至冠冕之位,將神的涌流帶到世間,只有這樣世界才能存續:這些對性的露骨描寫與過分強調徹底改變了卡巴拉的走向。而抵抗黑暗唯一的方法,就是遵循猶太戒律,將惡的雜質分離出去——正如之前所說的那樣,阿布拉非亞削弱了選民的特性,而光輝之書不僅大大強化了它,還在延續塔木德選民觀的基礎上加劇了選民與外邦人之間的矛盾。

布拉格中心與冊法特教團
神聖羅馬帝國首都布拉格的猶太區是隨著政治中心轉移而一並發展起來的,此前德國猶太人集中在靠近斯拉夫地區的雷根斯堡和德國西部的沃穆與阿爾薩斯。大約在十六世紀時期,文藝復興以後,宗教改革開始,除了新科學崛起外,此時占星術,鍊金術等神秘主義學說再次在德國興起,而於帝國中心地區的猶太人也受到影響。盡管沒有出現新神秘主義運動,但是在神秘主義方面的發展令人矚目。傳統德國猶太人的神秘主義思想發掘繼承,與其時的神秘主義思想糅合,其中不少是以實踐性的魔法手稿的形式為人所知。除此之外,天界的參訪者(Magid)在這段時期的敘述中很常見,往往是天使或是先知厄里亞烏(Eliyahu ha-Navi)顯現給當事人,為當事人講授關於神秘主義與天上的律法主題相關的內容。而這個時期最著名最重要的猶太神秘主義者,自然是布拉格的賢者(Maharal)。
布拉格的賢者本名為猶大列維(Maharal),意思是猶大族的雄獅,出生於德國沃穆地區,沒有經過專業訓練,屬於自學天才。他後受到任命前往布拉格統領當地猶太社群,因此舉家遷往布拉格,並與當地要人結識,成為皇帝與貴族的座上賓。他與天文學家第谷是交好,並且時常與第谷探討天文學,還同克卜勒有書信往來。同時他也曾為沉迷各式研究和娛樂的游手好閒的魯道夫二世講授卡巴拉與神秘主義學說。同傳統猶太人不同的是,猶大列維不反對尊敬基督教統治者。在他看來,這些統治者就是神明所任命的,無論他們給當地猶太人帶來的是痛苦還是自由。同時,由於他的卓越地位,後世傳說中他創造了一個巨大的類人偶(Golem)保護布拉格猶太社群。這是類人偶中最負盛名的傳說。
猶大列維在他的思想里面結合了中世紀哲學與傳統德國猶太思想,因此其作品獨具特色,在當時的猶太人中找不到類似的想法。在他看來事物總是呈現出相對狀態。邊緣與中心,光與暗,物質與精神,陰與陽,事物總是有其自身配合的屬性,而在其中會有一個平衡,就是第三屬性。以此種三分法,他同時將宇宙三分,分別是物質世界,介質世界以及靈魂世界,也以此三分了人體——同時代的帕拉塞爾蘇斯,傳說中燒瓶小人的創造者也有類似的理論。毫無疑問,該理論刻有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印記,盡管它常常被分配給卡巴拉三柱理論。這種三分法在中世紀基督教神學中曾經非常流行,並影響了當時歐洲的神秘主義學說,其理論根源在於神的三位一體。因為神是三位一體的,因此神所造的萬物,包括宇宙,都表現出神所意欲表現的真理的傾向,也就是呈現出三一特性。這種三一的另一種區分法則是對時代和存在進行的討論,此類學說影響了後世哲學家,例如謝林的世界時代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由此亦可見當時德國猶太人與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復雜關系。
猶大列維的理論以書卷的形式被寫下,他的教授在德國猶太人中流傳,並影響到後來的神秘主義運動,尤其是他受到邁蒙尼德的啟發後從聖經研究中得出的拯救的預言,認為猶太人得到拯救並最終成為世界的永遠王者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是古代智者早已發現的歷史的必然規律和最終進程。後世的東歐猶太人與立陶宛猶太人對於原始猶太神秘主義的理論模型的理解就有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他的解說之上的。在稍晚時期的德國文學與新教文學中有大量託名猶大列維的所謂隱秘智慧卡巴拉,里面有相當多新思想新改革與完美世界的理想,但不過是利用德國人的葉公好龍而進行的出口轉內銷的生意,此熱潮一大影響就是導致虛構組織玫瑰十字會被許多人信以為真,並認為那些作品真的是教會不希望人得到的隱秘神聖智慧。

在西班牙猶太大流散後,許多被迫離開的猶太人前往北非或是回到以色列地,並為失去產業而感到痛苦。救世主運動和末世論在此時非常盛行——實際上早在光輝之書的時代就有大量的末世論出現,光輝之書的作者自己就在其書中預言該世代為最後的世代。在大流散剛結束的時候,就有號召救世主運動的猶太神秘主義者,但是響應者寥寥。此時的猶太民眾不再對公開的神秘主義事物感興趣,加上時局不利,猶太神秘主義者開始趨向於聚集小圈子進行活動。
冊法特(Tsefat)卡巴拉城就是如此建立起來的。最初冊法特只是奧斯曼帝國接受西班牙猶太人以後集中堆積的小城,因為聚集人口眾多的緣故,開始建立起巴勒斯坦地區的經師法庭。該地最早的卡巴拉代表人物是雅可夫貝拉不(Yakov Berab)一個富有的經師。後來貝拉不把這座城市的法庭交給了他的弟子約瑟夫卡羅(Yosef Karo)。卡羅在此建立了一座經典學院(Yeshiva),並組織了最早的冊法特教團,許多人慕名前來,並將此地的法庭作為最高指導。卡羅除了這些工作外,也寫一些阿拉伯語的神秘主義著作,但他最著名的事跡當屬他受到一個自稱是來自天堂的口傳律法之靈(Magid Mishna)的引導。這個無形之靈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嚴加干預,附身並控制他的身體,以卡巴拉的角度寫下如今在猶太人中最權威的法典大全《預備餐桌(Shulhan Arukh)》,甚至這個靈還發生過和他爭搶身體的情況。不過也正是因為這個獨特的靈物,這部法典被賦予至高無上的地位,此後一切律令都被禁止討論,眾人只有一個實踐權威。
約瑟夫卡羅的後繼者摩西科多維洛(Moshe Cordovero, Ramak)是和布拉格的賢者幾乎同年的人物,他曾在歐洲停留一段時間,可能是西班牙流散的親身經歷者。他一開始並不了解神秘主義,他只是一個塔木德學者,但在一次聽見天使的聲音,讓他去研究光輝之書以後,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對神秘主義的研究之中,並以其天才獲得了贊譽,成為冊法特教團的領導者。
科多維洛和約瑟夫卡羅一樣,都是有救世主情懷的男人。約瑟夫卡羅的救世主情懷體現在他想要大一統律法而寫書——塔木德傳統里面認為律法的恢復意味著救世主的臨近,而邁蒙尼德曾經也做過這種大一統,不過顯然沒有卡羅成功——而科多維洛則以統合並體系化光輝之書為己任,實現卡巴拉大一統,將隱藏的秘密顯露出來,實現「神是一,他的名號是一」:這又是一個救世主式宣言,在卡巴拉傳統里面只有救世主時代,秘密才成為大眾可以理解的知識。毫無疑問,這種救世方式比做一個普通日本高中生困難多了(盡管日本高中生使用的很多不知所以的東西都是從他這里來的),科多維洛用了相當的精力整合,並寫下許多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石榴樂園(Pardes Rimonim)》。
石榴樂園實際上是卡巴拉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對於光輝之書碎片式理論的統合分析展示出科多維洛以邏輯處理神秘主義這方面的天才,同時光輝之書碎片化的思想被科多維洛賦予了神秘哲學含義,這種方式使得看似漫無目的的思維碎片呈現出一種秩序,令讀者可以透過對這些碎片觀察而看到潛藏於這些葉片下的枝幹。這正是科多維洛的目的,「讓眾生不至於迷失在光輝之書那浩大思想的無垠之海中」——不過顯然,這種成體系化的思想可能並不是光輝之書作者本人,或者說萊昂的摩西自己的想法,而在他的頭腦中可能也未曾浮現過在科多維洛頭腦中那麼清晰的思維脈絡,這也導致科多維洛在這些問題上思考的比萊昂的摩西更遠。
正如之前所說,末世論和救世主運動構成了西班牙流散以後的卡巴拉思想基礎。此時過去的哲學家的玄思已經不再受歡迎,人們迫切需要真理能真正解答他們如今的處境,以及如何面對它。石榴樂園無疑是回應這一問題的努力。科多維洛通過整合光輝之書里面的新造神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細致分析,並將罪惡之根挑明在人眼前。這一理念的詳細描述,便是所謂的善惡知識之樹,而統領此世界的天使梅塔特隆出於保護地上之法做出的決斷,因其忽略了天上之法而導致助長了黑暗力量蔓延,上升至諸界。
在卡巴拉里面,生命之樹(Ets Hayim)是由十個散射構成的。這並不難理解,因為通過這十個散射,世界與神聯系在一起,這十個散射就如此顯現。而令人墮落的善惡知識之樹(Ets ha-Daat Tov ve-Raa)則與之相反,令世界與神隔絕,遮蔽世界的光芒。它最原初是裹覆各個散射的殼(Klipot,單數Klipah),是神的力量自然生成的。正如種子需要從外殼內長出,生命之樹完成需要發散,於是下七位散射生成時就從內部破壞了殼,這些殼就脫去並沉積在底部。善惡知識,本身就意味著對立和隔絕,破壞了世界的完整和一體,本身「神的光芒普照天地」,世界都在神的光輝之下,但如今卻為黑暗騰出了存在的空間。因此出現區分,將神的照耀歸為善,而黑暗則沉降,「大地空虛而混沌,深淵一片黑暗」。
惡的激發是第二日出現的。在現今的希伯來版本中,創世紀第二日里面,神沒有說好這個字,光輝之書將之解釋為,第二日和第三日是連續而統一的工作,因為第二日和第三日是將水分開。在這里,經過摩西科多維洛的解釋,這里分開的兩股水,其實是兩股涌流,分別是左側的憤怒之柱的神聖涌流與右側慈悲之柱的神聖涌流。第三日顯露出乾燥之地,意味著隱秘的知識顯露,中間的平衡之柱浮現。但是第二日的時候憤怒之柱沉降下去,力量不受慈悲制衡,激發殼組成的混沌原初之海,而生出了暗影界的連續十個國王。這十個國王就對應了上界的十個散射,構成了智慧之樹。這一面也被光輝之書稱作是另一面(Sitra Ahara)。此處的另外的(Aher)並不意味著對等的,在希伯來語里面但凡這個詞作為特稱的時候都有遺棄的意味。
當這個另一面出現的時候,就是所謂的撒瑪厄勒與莉莉特結合所化的無明邪龍(Tanin Iver)顯現的時候,它就以迅猛的形式順著生命之樹往上。它同化了王座,攀上基礎,並沖擊中間的憐憫。正如之前提到的光輝之書所描述的那樣,神擊打它,它就掉落下來,纏繞這個世界,同化神灑落在這個世界中的神聖火花——也就是讓人陷入物質的惡欲,以令靈魂與包裹靈魂的物質,也就是殼,實現同化——這就是殼通過吸收光芒來維持自身存在的方式,也是為什麼殼一共有十一個部分,因為其中一個部分是被殼捕獲的散射。光輝之書對此說法的理論來自於經書中在論述以色列世家前在描述厄東十王,由於厄東和以色列對抗,在卡巴拉中被賦予了消極的,對抗於神的含義,因此光輝之書將這十個王對等於在神的統治鋪撒大地之前垂於黑暗的黯界十王。

黯界的十個國王分別如下:
其中撒瑪厄勒並不是從殼而生的,殼並非他的本性,他是為了聚集一群附和他的惡魔而違逆本性降入混沌的,而莉莉特則是由殼所生,因為她原本采自混沌之泥,後來被遺棄。他和莉莉特被稱作墮落的始祖夫婦,他們有一對最強有力的後裔,分別是地獄魔王亞斯魔德(Asmode)與被稱作小莉莉特的黑暗女王伊格拉特(Igrat),後二者也是一對邪惡夫妻。撒瑪厄勒甚至常常出於嫉妒和覬覦而與他的雌性後裔伊格拉特交合。除此之外服侍撒瑪厄勒的還有娜瑪(Naamah),淫女(Rahab),馬哈拉特(Mahalat)。她們不僅滋生黑暗,也誘惑人類,奪人性命,折磨有罪的死者。
十個國王是下面七個散射的殼,它們組成的知識之樹本質上是為了上溯並包裹各個對應的散射,吸取它們的光輝,維持自身存續。這就是亞當夫婦在樂園中看見的爬上生命之樹的蛇。殼的性質如同一種趨於冷卻的岩漿,當它遠離神聖之樹的時候,因為缺乏神聖的滋養,便會僵化而消滅,因此它如同尋求重物以堅實基底的沼澤,不斷捕獲來自上界的光以增添自己的力量。人類進入世界便是被殼捕捉並陷入肉身之中。人越是對罪惡迷戀,靈魂本質的火花就越是被冷卻同化。而死亡時,則是將火花從肉身中取出,投入煉獄之中熔煉。同化的越多越難解除,而完全同化者則會在熔煉後消磨殆盡。
逆轉這一過程的方式便是接引神之光芒,通過踐行律法以完成淨化,正如光輝之書所寫的那樣。實際上,回到之前所提到的,猶太神秘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認為末世與拯救本質是再創世,要進行對世界的拯救,就要知道世界的創造,而世界的創造是建立在散射對神聖光芒的引導之上的,而人被造出來就是為了幫助完成這一目標。因此實踐戒律成為了人受造的原因——又一個塔木德神話,神選擇創造人是為了人能在世界上遵循誡命,而最後只有猶太人選擇順應神的要求——而那些沒有完成的靈魂就會變成被罪惡抓住的死靈(Dybbuk),沉淪在混沌的黑暗之中。
但這似乎還是沒有完全解決救世主的問題,也沒有解答每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個人來到世界上是來做什麼的。因此,在科多維洛死後,一個遠道而來的天才青年迎面看見了送葬的隊伍,他同時看見的還有其他人看不見的科多維洛寶座上方的火柱,這意味著他就是科多維洛預言的先知,科多維洛的繼承者。而他的名字則是伊察克盧里亞(Itshak Luria),後世稱他為聖者雄獅(Arizal)。他是歷史上最重要的卡巴拉教師,因為今日幾乎所有卡巴拉理論都是在他的思想上發展出來的。

盧里亞據稱是一個有神通的人。他早年在埃及生活,受到先知的啟示者指導,然後接受啟示,從埃及上來,到達冊法特,接替科多維洛的領導者之座。他可以透過將手放在人的額頭上面看見這個人的前世和這個人此生的任務,還能看見隱藏在田野中不被人發現的,光輝之書中所記錄的賢者的墓地,並與該處的賢者靈魂交談——然而這些賢者不少都是萊昂的摩西虛構的。他自稱是摩西的轉世,也是光輝之書中主線故事的主角,若海之子西蒙的轉世——而光輝之書把西蒙稱作是神的顏面,盡管無論歷史還是塔木德的記載,西蒙都不是一個如同光輝之書描述的那樣特別出眾的人物。
他聲稱摩西只是接受了律法,並沒有教給以色列人其含義,而他就是來揭露律法的真正含義的——他生在邁蒙尼德之後,顯然不受「從立法者摩西到邁蒙之子摩西」這句話的約束,同時這個表述又隱晦的揭示了他的救世主情懷。他禁止他的弟子閱讀冊法特教團以前而先知邁蒙尼德以降的卡巴拉作品——不過光輝之書這部被認為寫成於一世紀的書是例外。其禁止理由是「那些都只是那些人腦中的想像,因為他們沒有先知啟示」,即使從他自己的語錄體教導來看,他自己的想法也往往相互矛盾。他還禁止學徒研究實踐神秘主義,理由是「這個世代已經不夠聖潔,無法維持對於先輩的神秘主義實踐,因此操作神秘主義不僅危險還非常褻瀆」,盡管他本人卻以看面相看手相而著名。然後他因為透露秘密過多,激怒了控制這個物質世界的邪惡的死亡天使,因此過早結束了生命——這是他的弟子的說法,不過有件事是確實的,那就是他死於四十八歲,在那個年代還不算老年人。
盧里亞的學說有三個獨特而開創性的內容,它們就是盧里亞學說的核心,是對這個世界的創造奧秘的描述,也是對於拯救的指引。它們就是收縮(Tsimtsum),破裂(Shevira)以及修復(Tikkun)。
收縮理論是一個簡單到有點粗糙的理論。盧里亞認為,既然在萬物以前只有無限者,而無限是如此無限,那麼就不可能存在萬物生成的空間。因此在最開始,無限者在自己內部收縮出一個空間出來,這個空間就是宇宙後來的形象。盡管神收縮出一個缺乏神的境界,但是缺乏神是無法存在的,因此這個世界中依然存在神的光芒的映射。用他原話說就是:「雖然香油被從瓶中倒空,但是瓶子里面還有香油的一點殘留和香氣。」這是一個為了調和泛神論的折中說法。
隨後,神對這個世界進行光輝投射,這就是第一次的創世。一開始出現的是原初之人(Adam Kadmon),它是原點的原點,透過這個原初之人,原始的面容,純然的慈悲,神的光芒形成了原點的世界——類似一個早已在阿拉伯蘇菲中存在的概念,穆之光(Nur)。隨後出現的是三個上位散射,它們分別是大臉(Arikh Anpin),也就是冠冕,又被稱作神聖的古老者(Atika Kadisha),因為它是神聖形象的純然聚集。父(Aba),也就是智慧(Hokhma),以及母(Ima),也就是理智(Binah),參與到這個組合中。它們構成了神最原初的形象,與下界隔開。
進一步,則是小臉(Zeir Anpin),它是以憐憫(Rahamin)為中心,聯合其他五個散射構成的,發散神聖的光芒,它也被稱作應受贊頌者(Barukh hu ha Kadosh)——這原本是古代傳統稱呼神明的敬語。它們構成的也被稱作新郎。最後則是新娘(Nukva),也就是最後一個散射,王國(Malkhut),這個世界,同時也是神自我表述的最後一步,神的顯現(Shekhina)。這其中的秩序也構成科多維洛理論中的四重世界——在盧里亞那里變成了包括原初之人的五重——至高的原初之人,分離創造與創造者的臨近層(Atsilut),作為神之寶座的純粹的創造層(Beria),天使與諸宮廷所在的構造層(Yetsira),以及物質世界的發明層(Asiya)。每一層世界都如同一層面紗覆蓋在原初之人的面孔上,使得神的形象在不同世界顯示出不同樣貌,而總的來說是隱藏在這諸多樣貌之後的——這個理念衍生出靈魂之根的說法,而它們根本來自於安達盧西亞蘇菲伊本阿拉比。
接下來就是破裂環節。神的光芒照耀,進入小臉,此時小臉是以審判的力量為領袖的,因此神的光進入的時候,將它們這些容器(Kelim)震的粉碎。殼(Klipot)因此化作碎片降落,沉積在最底層,變成深淵下的黑暗王國。這是因為審判的力量導致平衡失去而造成的,但同時這也是一種新生,如同種子發芽而破壞了果殼。惡從神的創造中獲得了形式。
但神的創造並未因此中止,發散繼續進行,小臉再度構造,平衡了力量,進而形成了最後的王國。王國中出現了人——這是創造的末端,而修復的任務此時趨於尾聲。之所以人是創造的末端,是因為神本是無意識的自然理性,通過不斷進化,在人身上實現自由意志,由是人是神的形象,承載神修復世界的重任。創造的過程持續進行本身就是修復,而為了實現修復,人需要遵循律法,在正確的時候,也就是安息日,新娘和新郎交合的日子,吃生命之樹的果實,也就是持守中道。通過人的這個行為,神得以具有意識並認識自身,這樣世界就進入了永恆的安寧,惡不再能進入這個世界。但顯然人沒有這麼做,因此世界進一步被破壞並損毀。因此,第一人(Adam Rishon)的錯誤導致火花散落在世界中,被黑暗所占據。原本的火花是一片延續不斷的光,因為墮落而被肉身包裹分隔,變成相互獨立而封閉的一坨坨的光。
最後需要進行的,就是居住在大地之上的人的修復。在這里,不再是對一個遙遠的救世主的期待,每個猶太人都可以參與到這場修復之中。不過這場流散和囚禁並不唯獨發生在猶太人這個群體上,更是整個世界以及每一個人的現實處境,它和每一個生靈息息相關。猶太人命定來實踐律法,進行祈禱(Tefila)和內在的沉思(Kavana),降臨到靈魂根部,與神進行神聖而隱秘的會晤,將世界的秩序一點點修正。由此,救世主運動成為一種全民性的運動,這一運動不再是所有人一起等待救世主到來,而是發動所有人一起打造一個地上天國,以迎接救世主到來。
而沒能完成這些的靈魂,則會一次次的在大地上輪回(Guilgoul)。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靈魂特性選擇和自己同享原型靈魂的聖者墳墓,在他墳墓上祈求,這樣聖者的靈魂就會暫時性降臨在此人身上,這種方式叫做遷移(Ibur),而通過這種協助人得以完成律法,這種方式叫做恢復(Tikkun),也就是通過持守律法完成對破碎世界的修復。同時,死獄(Gehenna)也變成輪回的一種隱喻,人根據罪過不同而決定輪回到人,動物,植物,或是礦物之中——這種萬物有靈的觀念也建立在一切事物都是被束縛在不同形體的神之光這種理念上,一種泛神論。當然,這也意味著對於更早之前的塔木德傳統的拋棄與改造。
通過這種方式,盧里亞開啟了一種新的救世主模式。他的理論有著深刻的諾斯替思想在其中,讓人不時想起瓦倫廷與摩尼,並且末世論思想隨著這種輪回說而逐步重要起來——但這並不是傳統的末世論。因為輪回是為了完成律法並為自身贖罪進行的——換言之就是佛教所謂的因果業力——因此他認為,西班牙大流散就是一次潔淨業力的果報,這意味著救世主的世代臨近了,只要對他寫的經文多加誦念,清除業障,就可以促成救世主到來。這一理論後來也被一些重要的當代猶太經師解釋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的清洗(Shoah),認為其是對猶太人贖罪的方式,或是這些人通過這種死亡而贖罪升天。不過顯然,這種言論受到輿論抵制。
雖然卡巴拉的輪回可能是糅合了諾斯替與畢達哥拉斯學說,甚至還有一些從突厥部落獲得的啟發,但是它在猶太歷史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盧里亞在將輪回與救世運動結合後指出,猶太人在此世界反復輪回,其目的甚至不再僅僅是為了清潔自己的罪業——否則無染罪業的賢者的輪回將難以理解——而是為了將世界帶入救世主時代。這意味著,猶太人出現就是為了拯救這個世界,而拯救這個世界就是猶太人出現的意義——這讓人想起塔木德中「世界是為猶太人而造」,「殺死一個猶太人就是試圖毀滅世界」這種強調選民身份的說教——這也導致卡巴拉得出了一個影響後世深遠的結論:哪怕一刻沒有至少十個猶太人祈禱,那麼世界就會毀滅。而安息日則是神的喘息,在這一日神的光終於可以在猶太人的幫助下通過黑暗遮蔽而射入世界,但在其他六天內,這個世界被黑暗包裹著,如果這期間沒有猶太人支撐世界,則後果不堪設想。
但非猶太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外人的靈魂和猶太人從根本上就不同,並非真實完全的人,因此外人只能輪回三次,隨後靈魂就會完全熄滅。也因為這個原因,猶太人自始至終都會成為猶太人,因為猶太人的靈魂是神聖火花,它和混沌之泥塑造的非猶太人根本不同,也完全不能相容:「因為光明之子不會尋求黑暗。」這是建立在光輝之書對出埃及故事的寓言上的:「猶太靈魂必然的使命就是出走黑暗的埃及」——但同時沒有黑暗的埃及就沒有猶太靈魂,或者說,除了以色列,滿地都是意圖殺死以色列的埃及。這個直接來自光輝之書的結論很自然的將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一切對立,並間接導致了後續的一連串對立事件。
盧里亞死後,他的卡巴拉理論被他的首席弟子哈因維塔(Hayim Vital)壟斷,不准其他弟子詮釋,也不公開,直到這位弟子死去以後,有盜版手稿流傳出來,才掀起熱潮,而真正的維塔手稿則在很晚以後才公之於眾。但在其生前,冒名盧里亞的教導就已經流行,而現代卡巴拉大鬥受過它們影響。冊法特教團後來壓過了其他所有地方的卡巴拉教團,在猶太世界一支獨大。因此,埋葬了這些教團領袖的冊法特被形容為「連空氣都是神聖的」——前段時間才有一個朝聖者在抵達冊法特沒有多久就因為身體不適而心肌梗塞,這或許說明冊法特大氣中的神聖因子含量已經高達足以致死的地步。
歸功於他的救世主理論,以及他對於末日將發生在一五七五年的預言——歷史上自信滿滿的卡巴拉教師經常預言救世主世代,但是從來沒有應驗過,即使這個人被認為是神在地上的使者——導致救世主運動比過去更加活躍,並更能抓住猶太人的心。因為這個原因,盧里亞的理論一經解放就很快散播出去,並最終幾乎成為一種猶太全民的信仰。這也為後來被猶太經師在其失勢後斥為邪道的沙巴泰運動掃清了道路。

沙巴泰茨維,被唾棄的救世主
沙巴泰茨維(Shabbatai Tsvi)是盧里亞理論病毒式傳播以後出現的一個人物,他對於整個卡巴拉理論的影響不亞於盧里亞本人。這個只研讀光輝之書而不接觸塔木德的經師的精神極其不穩定,他時而會感到狂喜,時而會感到消沉。在起初,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救世主,可能一點相關念頭都沒有,只認為自己是神性上有缺陷的人——不過這段歷史對於今人而言不夠清晰。他失勢以後,所有文檔被所謂的「正統」全部銷毀,導致其人的生平難以琢磨,在主流社群中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歷史人物,因此只能通過學術研究的成果了解這個時代。
沙巴泰成為救世主的過程非常戲劇性,完全不取決於他本人,他是被他的第一崇拜者推舉為救世主的。最初沙巴泰作為經師只是被所處環境的猶太人所嘲笑,是一個被議論的對象,因為他精神不穩定,時常狂躁時常抑鬱。但直到他遇見一個名叫加沙的納坦(Natan de Gaza)的年輕人,事情才發生改變。這個年輕人是一個天才,他無論是經典還是神學方面都有相當的創意和水平,並且還是一個真正的神秘主義實踐者,經常體驗天使和神的異象。現代正統派拉比猶太教在論及這段歷史時,總是會把整個過程描述為,一個瘋狂的猶太人以他對自己看過的神秘文本的粗糙印象哄騙了一個年輕人,這激起了年輕人心中的火焰,於是開始了一場出於誤解和反對的運動。但這並不是事實,因為沙巴泰的才能不夠出眾,甚至可以說在納坦面前顯得十分平庸。真正導致這件事發生的,是在納坦還沒有見到沙巴泰這個人的時候,在天使指示的異象中看見了救世主的樣貌。後來他經天使指引抵達耶路撒冷以後見到沙巴泰的真實面貌,堅信沙巴泰就是救世主,因此鼓動沙巴泰宣布自己就是救世主——而沙巴泰主動來找納坦則是因為他聽說有一個來自埃及的大師在耶路撒冷,他希望能讓這個大師治癒他神性上的折磨。
沙巴泰變成救世主以後並沒有在一開始就引起大眾關注。當時這個性情陰晴不定的人不斷在極端情緒下公然違抗猶太律法,在恢復冷靜以後又為其感到悔恨。真正使得它改變的是納坦的解釋。按照納坦的解釋,這完美的符合了盧里亞對於世界進程的描述。神聖的火花跌入谷底,而最神聖的原初之光,救世主的靈魂,則進入了最深的地方,被黑暗的靈魂所折磨。當它表現為沉寂的時候就是被黑暗包裹的時候,而當它活躍的時候,就是神性的光輝照亮救世主的理智的時候。同時,救世主對律法的破壞也是積極的,因為救世主的到來就是為了宣布惡籠罩的舊秩序失勢,過去為了隔離純淨與污穢的律法將在新紀元失效,因為沒有污穢和相關的禁忌存在於救世主的世代,因此救世主此舉就是以奧秘的方式消滅了惡的力量——這種對於傳統的否定和背叛一直存在於猶太思想史中,並被後世猶太神秘主義者稱為是神秘的進步與革新。
這個運動興起的時候,幾乎席捲了整個猶太世界。從伊拉克到德國,幾乎只要有眾多猶太人聚集的社群,就會有對於沙巴泰救世主的信仰。對於那個時代的猶太人而言,尤其是經過之前的劫難並留意其所處的困境,就難以避免在聽到救世主到來這一喜訊後陷入狂熱並奔走相告。伴隨這個信仰一起廣為傳播的還有光輝之書以及盧里亞理論,因為沒有它們,要理解這個救世主就是不可能的。這導致東歐猶太人中產生出對於救世主運動的狂熱,而在德國猶太中心,布拉格和盧布林,傳統德國神秘主義者卻大力抵制,禁止社群成員閱讀或是談論光輝之書以及相關內容——而這個時期的布拉格猶太人則是留下了諸如《神聖的種子(Zera kodesh)》這種類型的實踐神秘主義文本,其內容有不少升天與創世技法的影子。
一六六六年,對於猶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奧斯曼土耳其的蘇丹聽說了猶太人中大規模爆發的救世主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混亂,因此決定親自動手。他將沙巴泰召到他面前,對他發問說:「我聽說猶太人的救世主到來的時候,是會行使奇跡的,甚至能把被斬斷的頭自己接上。既然你自稱是救世主,那麼我就試一下:如果你是救世主,那麼就在我面前把你自己的斷頭接上;如果你拒絕,那麼你就不是救世主,你要禁止你的門徒的宣傳,並皈依我們的教導。」沙巴泰屈服了,皈依了蘇丹。此時有一大群人跟著沙巴泰一起皈依了蘇丹,而歐洲的追隨者則大舉皈依天主教——此舉震驚了當時所有猶太人。早年幾乎大半個猶太世界的人都支持或默認他是救世主,在這個事件發生後,這些人立馬同沙巴泰保持距離,並宣稱從一開始他們就拒絕沙巴泰這個虛假救世主,真假教導的戰爭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
正統和異端在沙巴泰問題上的戰爭從一開始就存在——這顯然不是真的。這言論不僅不是真的,而且在當時許多非常重要非常有地位的家族和經師都支持這個運動,甚至今天的每一個卡巴拉學者頭腦中都有沙巴泰的印記。但如果接受這樣的說辭,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沙巴泰皈依以後帶動了大部分追隨者皈依。在納坦所教授的沙巴泰救世主神學中,早在為解釋對律法的反抗時,就已經包含了解釋此行為的可能。救世主的靈魂為了拯救一切被困在深淵中的靈魂,就必須親自降落,背負罪人之名降臨到最深的黑暗之中,在那里戰勝深淵的力量,通過這種方式將囚禁靈魂的黑暗牢籠打破,然後升起。
在這里,沙巴泰的追隨者使用了一個在卡巴拉中非常常見的描述:神聖的蛇(Nahash ha- Kadosh),因為在卡巴拉看來,蛇的數值和救世主(Mashiah)是一致的,因此救世主的象徵就是蛇,是被摩西掛在手杖——生命之樹的一個象徵——的生命之蛇。不過在這里,這個詞增添了新的意思。為了打破一切黑暗,救世主必須降落到黑暗最濃厚之地並將之打破,這就是神聖之蛇的使命。因為深淵的蛇屬是直行迅猛的大蛇,是扭曲隱藏的大蛇,是深淵之龍,因此神聖之蛇降入深淵之蛇的巢穴中,由於蛇的特性而顯得和這些黑暗極其相似——這便是神聖的罪人,是先知預言的未來要承負罪人之名,因此受苦而拯救世界的救世主。他的罪過無不是為更深層,更崇高的目的而做的,因此要出離最深層的黑暗,就要進入最深層的黑暗,換言之,就需要背棄原本的神聖教導。
毫無疑問,這讓人想起了諾斯替派的猶大福音,猶大出賣耶穌被認為是為了更深奧的救贖而做的,因此猶大是最偉大的門徒,他背負的是最沉重的罪惡,隱藏的是最深刻的秘密。值得注意的是,沙巴泰和耶穌在惡的事項上有根本不同。耶穌本人對於惡是無染的,他的罪是外界附加的,而沙巴泰則是主動破壞戒律,沾染罪過,盡管他是無意識的。這里涉及長期以來猶太傳統中神賜予人間的律法與神保留在天的律法的對立問題,盡管塔木德就宣稱「律法賜給猶太人以後天上就沒有律法了」,但是這並不能阻止,反而因為現行思維無法解釋天意導致的現狀,而加劇了這種撕裂。沙巴泰的行為有意無意突出了這個矛盾並通過納坦合理化,使得破壞地上的律法變成了為了彰顯天上律法的途徑,新的事物變成對於舊的事物的絕對否定,這直接導致後來猶太人中出現的以反律法與反經典為主要途徑的發泄。
由於類似的理由,沙巴泰的追隨者效仿他的行為,背叛並破壞戒律,認為這是響應盧里亞的教導——每個人都做自己的救世主,一起將世界提升起來;不過也有遵循舊教導的人,認為這麼做是為了不給惡留下把柄,因為只有救世主進入了那種不受污染的境界。這種種行為都與基督教教父對諾斯替的記載所吻合:縱欲或是禁慾,都出自同一個諾斯替教導。但無論是保持舊教導還是選擇進入新教導,毫無疑問,這些教導對他們而言都是虛無。他們根本不在乎也不相信這些,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按照沙巴泰的途徑沉入黑暗,並通過這種偽裝和欺騙做外衣傳播自己的教導,好將光輝提升起來——這種塔基亞行徑是對於他們所處的外在環境的深刻腐化,自然,這些皈依者不為基督徒或奧斯曼人待見,也不受其他猶太人待見。
有一點或許會讓人感到困惑:救世主既然到來,為什麼末日沒有出現?這不得不歸功於盧里亞的發明。盧里亞將傳統的物質世界恢復關系顛倒,認為對於世界的恢復首先是從散射之類的抽象要素的恢復開始的,現實世界的解放和恢復只是這些具有決定性質的抽象要素恢復(Tikkun)的結果。換言之,物質世界的恢復只是恢復的一個結果,它不是恢復本身。恢復本身要做的是將精神世界的善和惡分離,一旦這個世界的善惡分離,王國從深淵的包裹中升起,亞當未能完成的使命得以完成,那麼整個宇宙秩序的恢復和解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恢復本身,正如盧里亞所教授的那樣,在於每個人內在的火光升起,所謂的「救世主的火花」,靈魂的根本。這個運動本身就是一場神性的運動,一場每個人內在力量的運動,因此救世主的到來不再直接導致物質世界的改變,他的到來意味著運動的開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沙巴泰背叛律法之後,沙巴泰的追隨者——因為身份特殊,他們構成了所在教團中的秘密結社——使用了一系列的新術語來描述他們的神性上的勝利。由於在這個運動中,許多人感受到了一種神秘的經驗,一種狂喜,因此在沙巴泰背棄之後,他們依然認為自身經驗了神性的解放和救贖。在他們筆下,救世主運動從一場社會性的運動轉變成一種個人的內在經驗——這不意味著他們就放棄了社會運動。事實證明,沙巴泰的追隨者在後來的各國社會運動,尤其是猶太社會運動中有非常多的參與,與當地猶太社群里應外合。這側面反映出,對於沙巴泰以及隨後的猶太人而言,精神上的覺醒是社會覺醒的先聲,這一切都如盧里亞所說的那樣,是修復(Tikkun)的進程——猶太救世主運動從沒想過要拋棄其中的社會性。
沙巴泰的追隨者使用並改造了一些傳統詞匯,賦予了它過去所較少提到甚至沒有的意思,例如:信仰(Emuna)。信仰原本在猶太傳統中是不需要的,對傳統猶太人而言,信仰並不重要,重要在於實踐誡命。但是沙巴泰的追隨者賦予了它新的含義,其中還包括對於神的無比的信任,對於神的拯救的期望,而最重要的自然是對於神本身的信仰——這其實頗有基督教思想的味道。另外,由於救世主的到來廢除了舊秩序,因此新歌(Shir ha-Hadesh)就非常重要,它不僅是對新秩序的歌頌,也意味著自身的神性覺醒,從而不再屈服於舊秩序下,是精神上的勝利。而一些在塔木德中被故意曲解的古老傳統在光輝之書中復活,並被沙巴泰採用,例如受苦的救世主,擔負罪人之名的救世主——為了避免被基督教使用,塔木德賢者故意以其他方式解讀這兩個預言,但在光輝之書中這兩個預言復活,並藉助沙巴泰運動再次公開出現在猶太世界。
沙巴泰在整個猶太世界造成的影響無異於一場精神核爆,通過他盧里亞卡巴拉滲透了幾乎整個猶太世界。他失勢以後迅速變成眾人提防的反面教材,並且各種對他的污衊興盛起來。在十八世紀時,伊拉克地區出現一場叫魂恐慌,當時的猶太社區為沙巴泰和納坦的死靈(Dybbuk)所折磨,這兩個不潔淨的靈魂因為自身嚴重的罪過不得安息,而在惡魔的驅使下騷擾該地區的居民。最後伊拉克地區的猶太驅魔人終於在逼問納坦的靈魂是否願意尊崇律法,得到否定回答以後,通過強制的行為將之逼迫出受害者的身體而宣告噩夢終結。至此,沙巴泰的夢魘終於不再在廣大猶太人民的頭上盤旋。
但義大利出生的拉比盧扎托(Hayim Luzzato)就沒這麼好運了。他和沙巴泰是同時期人,二者之間沒有交集,在他短暫的前半生中他曾被先知光顧,並在啟示下寫出其神秘教導,即《第二光輝之書(Zohar Tinyana)》。但他的同事發現其思想和沙巴泰運動一致,他不得不被迫發誓從此不進行神秘教學。他畢生帶著天使賦予的救世主理念流亡,最後死在以色列的阿卡,直到他的作品成為立陶宛流派的重要經典以後才得以恢復名譽。這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重要人物,和沙巴泰不同,他的理論得到承認,完成了沙巴泰運動所沒能完成的事業。他的理論認為世界的最終目標不是修復(Tikkun),而是在這之上與神合一(Yihud),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對盧里亞思想的補充和拓展,是其終極形式,也是對神主動破壞殼這一違反神義論的行為的最佳解釋。他對猶太倫理學進行了極大的拓展,賦予其神秘和深奧含義,並間接導致了後世的道德運動(Musar)。只是他的名號因為其經歷而長期被埋沒,不為人知。
沙巴泰失勢以後,一些地方首領模仿沙巴泰而自命救世主,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東歐的雅科夫弗蘭克(Yakov Frank)。這個人物以其厚重的虛無主義及激進言論而知名,在他口中誕生了諸如「法律被摧毀就意味著法律被實現」這樣的口號,並且曾一度引起俄羅斯大公的關注。東歐的哈西德運動與這個激進派別不無關系,並且在哈西德的救世主浪潮中也出現了幾個在沙巴泰運動中出現的關鍵字眼,例如信仰(Emuna),新歌,狂喜,這些特徵在哈西德創始人的小兒子,布列斯勒夫的納赫曼(Nahman de Breslev)所代表的精神覺醒運動中特別明顯。

烏克蘭的哈西德,立陶宛的密納格
哈西德(Hasidim)和密納格(Mitnagedim)是一組相對的運動,具體來說,哈西德比密納格更早。密納格是反對哈西德運動而生起的,因此其名稱含義為反對者。而哈西德的名稱含義為虔敬者,和德國歷史上那個虔敬者運動沒有任何關系——同樣名稱的運動在歷史上不止一起,實際上第二聖殿時期就有名為虔敬者的組織存在,不過也和後面這兩個運動沒關系。
這兩個運動的對立是圍繞對於光輝之書的解釋上展開的。密納格認為哈西德支持泛神論,因為哈西德認為神存在於每一處,每一個事物都是神的光,並且人的自我(Ani)不存在(或者說,是無Ain),一切都是神,這是對於神的赤裸裸的褻瀆;哈西德則認為密納格將神約束在宇宙之外,不可知而遙不可及,是對神的形象的歪曲——這其實是光輝之書以及數個世紀下卡巴拉累積的泛神論與邁蒙尼德的絕對無知一神論之間的矛盾的爆發,所以哈西德和密納格都可以在過去的卡巴拉教師語錄和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的材料。
哈西德運動的創始人,厄里亞扎之子以色列,或者他更為人熟知的名字,聖名之主,巴爾閃托夫(Baal Shem Tov),出生在今屬烏克蘭的當年波蘭境內的小村莊。如今這個創始人的生平已經不甚清楚,更多的只有圍繞他的傳說。傳說他是孤兒,是個天才,有天使為他教學,啟示給他神秘的奧秘,殺死並解脫了來犯的狼人,並且他帶著救世主的心態領導著整個社區——又是一個毫無創意的救世主的故事。按照說法,這個人參與了弗蘭克教團的論戰,並希望弗蘭克教團悔改。從他的弟子的回憶來看,聖名之主非常推崇的幾個卡巴拉作品,其作者都是沙巴泰的秘密追隨者。不過和沙巴泰不同的是,哈西德的英雄崇拜並不凝固在聖名之主身上,它實際上是圍繞各個社區領袖展開的,並且這些領袖或正義者在這個傳統中大都享有名之主(Baal Shem)這個稱號,和創始人一致。
哈西德創立的環境和當時其他地區的猶太社區不同。當西歐猶太人接受啟蒙運動,開啟猶太啟蒙運動,即所謂的哈斯卡拉運動(Haskala)時,東歐的猶太人還處於一種蠻荒狀態。當時的猶太人是以小型村莊為單位聚集在一起的,這些貧窮的猶太人大多是一些匠人,並且普遍文盲,因此他們很難完成經師傳統下的各種要求,比如對於祈禱和研讀經書的要求。出於這個原因,這些地區發展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傳統:讓經師代替他們完成這些要求和誡命。這就導致經師在這個傳統下幾乎變成了神人,負責天界和人間的溝通。
聖名之主化用的另一個內容,則是此前的沙巴泰的遺產。一方面,他以卡巴拉信條詮釋下的道德守則指導教眾,另一方面,他則將狂喜的經驗以及直觀的與神遭遇的內容引入他的教導,這二者很快就與普通民眾樸素的情感結合並迸發出火花。神秘主義不再是一種特權,而變成了一種人人皆可觸摸的事物,人人都可以遇見神。經師對於教條的詮釋讓位於神秘情感爆發,在這里,這場運動的核心——正義者(Tsadik),每個社群的精神領袖,往往擔任了經師的職責,他們指導教眾從事宗教活動——從傳統的教條戒律變成了在傳統儀式中與神直觀的接觸,而這種接觸的結果就是狂喜。
隨著運動開展,經師,或者更准確的說,正義者,成為了傳說的中心,他們的一言一行就變成了經書,他們出自靈感的詮釋和解讀變成了奧秘的啟示。這種個人崇拜使得這場運動分化為多個不同的派系和教團,而這些教團的領袖職位都是以家族形式傳承,比如山地教團(Satmar),或者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教團,哈巴德(Habad)。後者隨著自身發展壯大還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文本與創新。但無論如何,這些教導都是將其領導人視作是准救世主,先知,活著的經書。

密納格則是完全與之相對的一派思想。密格納創始人,所羅門之子厄里亞,或者他更著名的稱呼,維爾紐斯院長(Gaon de Vilna)痛批哈西德運動,因為當時的哈西德運動已經蔓延到立陶宛等地。為此,他與其所屬的卡巴拉社交圈建立了密格納派,意圖宣布卡巴拉是建立在塔木德和傳統經書學習以後的深奧知識,不是大眾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將卡巴拉封鎖在經典學院的大門里面,並以深奧的術語寫作,導致一般信徒完全看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他們也受到盧扎托的影響,強調猶太道德,因此從他們開始發起了猶太道德運動(Musar),試圖推進傳統道德價值的普及。
這一批學院派自身因其特殊要求改造儀式,因此和傳統德國猶太系統分離,他們也被外人稱作立陶宛派。他們痛批哈西德的個人崇拜,以及哈西德將性放在崇高地位這一舉措——但這完全是自欺欺人。自從光輝之書以後,性在卡巴拉里面有非同尋常的地位,不僅因為神和人的關系通過雅歌的影響被比喻為夫妻——此前夫妻的比喻只停留在以色列民族和神之間,而非個人層面,不過此二者也僅僅是停留在情感關系上面的比喻——還因為在邁蒙尼德化以後,神經過去人格化,變成一種依靠本能(Nature)行動的自然力量。此處的本能不是說,神因為是神,因此只做神本能驅使做的事情——而是一種更低級的原始沖動,例如,沒有理智監管的性沖動,這種動物般的本能,等同於叔本華說的生命意志。
因此,在卡巴拉思想里面,神依靠這種本能行動,而正義者對於神如同美人,神在覺察到正義者以後就會變成不能自己的發情生物,將它的光束投射到正義者身上,這樣正義者就獲得了啟示——此前基礎這個神聖的巨大器官只能將這些光注入王國這個神聖子宮之中,生成萬物。當經師處理具體問題時,將性完全神聖化,認為猶太男人與外邦婦女私通交合能將對方的神聖火花提升出來,而過去的衛道者不能看到這種神聖因而犯了誹謗罪。甚至對於性的發生,還有一系列細枝末節的指導,不遵循這些指導,孩子就是被黑暗力量污染的不潔之物:因為基礎(Yesod)是天上的巨大根部器官,王國(Malkhut)是神聖子宮,人進行行為就是要效法二者交合,也就是神聖的創造,而能夠效法的前提條件就是實行猶太人的割損禮,由此上下一同,不能效法則是在助長黑暗。而合適的交合方式可以引發新郎新娘(Zeir Anpin Ve-Nukva)的欲望,進而引發父母(Aba Ve-Ima)的欲望,最後刺激雌雄一體的原初之人(Adam Kadmon)自我滿足,將神的光帶入世界,這樣生出的孩子就是聖潔而受祝福的。
密納格在歷史上曾多次通過政治手段和宗教法庭牽制哈西德,並且二者因此成為世仇。猶太啟蒙運動(Haskala)崛起以後二者放下世仇,決定和解,因為在他們看來,猶太啟蒙運動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不僅要改造他們的傳統,還要將他們的靈魂依託連根拔起,葬送這個民族。不得不說,這方面這兩派有相當的遠見,因為啟蒙運動以後出現的唯獨理性主義思潮對於當時的猶太傳統的建設是破壞性的,其破壞性與這些神秘主義者的破壞性相當。

我們身處的時代
大約是在沙巴泰運動的一個世紀以後,葉門卡巴拉教師沙龍沙拉比(Rabbi Shalom Sharabi)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個重要的卡巴拉經典學院,神之舍(Yeshiva Bet El)。之所以選擇這個地址,一方面是因為盧里亞的弟子中有不少聚集在此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神之存在(Shekhina)被描繪為一個女性以後,盧里亞的弟子自稱看見它以一個黑衣婦人的形象在耶路撒冷哭牆(Kotel)下哭泣。
隨後來自猶太世界各地並具有一定地位的卡巴拉教師聚集在此,包括來自烏克蘭的哈西德創始人聖名之主的女婿。這個學院,或者說社群,不為一般人開放,它只接受高級卡巴拉教師。很快,這個學院一躍成為近東甚至是整個猶太世界最重要的卡巴拉中心,出版很多根本不給普通人看的作品,並對整個近東有相當的影響力,無論格局還是學術。沒有多久,這個組織的核心人物組成了一個十二個人的小團體,圈子里面的圈子。這個秘密社群以誓願相互束縛,結成一個十二人的秘密結社,愛慕和平者(Ahavat Shalom),並誓約相互分享,兄弟之間沒有秘密。
但是秘密依然存在。由其中三個成員,沙拉比,玫瑰哈因(Rabbi Hayim de Rosa)以及哈因阿祖來(Rabbi Hayim Azulay)自己結成了一個小同盟,實行儀式,意圖將救世主從天上拉扯下來。傳說天上有聲音對他們說:「現在不是時候,你們卻這麼做,那麼你們當中必須有一個人永遠流浪,不得回耶路撒冷。」於是阿祖來被迫流亡,在地中海沿岸流浪。這個學院挺過歷代動亂,並延續至今。在它的影響下,耶路撒冷成為新一代的卡巴拉中心。
十九世紀出現了一個特別的德國學者,在其他猶太學者秉持理性主義將神秘主義完全驅趕出猶太學術界的時候,將這批神秘主義迎入研究所並以之為研究對象,這個人就是Gershom Scholom。雖然他有受到尊崇哈西德的馬丁布伯影響(Martin Buber),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做的是一項幾乎沒有人做過的工作。他認真的研究了古代手稿,並整理了猶太神秘主義歷史,梳理了思想發展,將整個思想體系化。他的整理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和道路,讓無論學界還是教界中對此有意向的人得以找到一條門路。他在希伯來大學開設了猶太神秘主義研究學科,而稍晚一些的重要學者還有羅馬尼亞學者Moshe Idel則在他死後繼承了Gershom Scholom的衣缽,盡管他們二者觀點完全對立,Gershom主張卡巴拉根本上來自其他文化,而Moshe主張卡巴拉自古以來就是猶太文化的核心。
Gershom十八歲開始自學光輝之書,後來在慕尼黑大學以光輝之書為主題完成了他的博士學位。盡管他試圖在研究時壓制他自己的感情要素,但有時這些要素還是會體現在他的文本之中。他所做的是幾乎開創性的研究工作,而對他的理論的爭議也沒有停歇,並帶入到今日學術界對猶太神秘主義思想的研究。

哈西德和密納格依然存續至今,二者在以色列和自己的原生地繼續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烏克蘭與立陶宛的猶太區受到嚴重破壞,因此大批猶太人移居歐洲其他地方,或是遷往美國,英國,俄羅斯,以及巴勒斯坦。戰後這些移民隨著以色列建國而湧入以色列國,將他們自己的傳統帶到這個剛剛度過六日戰爭的彈丸之地,同時在這些新地點,他們之間出現磨合,並有新思想在其中出現。
糅合這二者的代表當屬巴勒斯坦第一任德系猶太人的首席經師,庫克(Rabbi Kook)。他的父親來自立陶宛傳統,而他母親則來自哈西德傳統。他從小在兩邊傳統交匯的地方長大,並通過兩方了解到不同傳統的區別和共性。一種新的傳統在耶路撒冷形成,並且仍在塑造之中。
立陶宛保持其封閉,而哈西德隨著移民而進一步壯大。如今只要有哈西德社區的地方,就會有頭銜為聖名之主的人物,負責干預和調節超自然事物——當然,他們避免接觸非猶太人。而哈西德初代領導人之子納赫曼(Nahman MeUman)的教導在新紀元運動以後(New Age Movement)被大力提倡,對於新歌,信仰,生活雞湯的寓言,以及最重要的,狂喜的體驗成為這個新運動的核心。在以色列街頭經常看到亢奮的納赫曼傳教士出現,他們鼓勵每個猶太人都加入他們的喜悅浪潮,並保持對於猶太身份的自信和自豪,正如納赫曼本人所說的那樣,「即使你一無所能,也要為你是猶太人而驕傲,因為神不會拋棄他的選民,只會更加關愛」。不過由於這個人物沒有一個統一的教團,因此實際上各個以他名號進行的活動都是私人而非官方的,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打著他的教導的名號出版印刷物。
真正走向世界並轉型的是名為哈巴德(Habad)的教團,他們因為在小鎮盧巴維奇(Lubavitch)出現而也被以該鎮的名字命名。這個教團以卡巴拉為核心教導,提倡修復世界等要素,努力將他們的成員能學到的任何內容揉進他們的體系里面。他們建立傳教團,修建猶太醫院和學校,向全世界派遣他們的傳教士以對各地猶太人傳教,並試圖將自己打造為最正統的團體——原因很單純,因為他們的末代領袖被相信是救世主。但因為他從出生到死亡都沒有迎來末日,因此這個領袖是約瑟夫之子(Moshia ben Yosef),前來受苦並將世界從黑暗中托起,而將在末日的榮耀中到來的是大衛之子(Moshia ben David)。他們相信存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地上的耶路撒冷兩種和平,每個信徒都在家中放置救世主的相片:這種種跡象都讓人想起被他們唾棄的基督教。這位救世主死並埋葬於紐約布魯克林,因此布魯克林有了一個聖墓,每天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上萬朝聖者。

隨著新紀元運動以及大屠殺帶來的幻滅,加上此前印度熱潮和卡巴拉的內核問題,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選擇將印度視作自己的精神聖地,每年有數萬猶太人前往印度追尋所謂精神的改變。同樣,受到這個風潮影響,在北美等猶太人密集的地方,許多猶太人選擇成為佛教徒,對他們而言佛教是認識神更好的途徑,盡管他們原始觀念中的佛教來自布拉瓦茨基的編造以及對印度諸神的誤解之上。這並不難理解,業報,輪回,尋找自己內在的神性,虛無乃至於不存在的神,以及非偶像崇拜,這些也都出現在卡巴拉之中——在猶太經師媚俗的判斷下,基督教是多神教和偶像崇拜,但是印度諸神和佛教不是——再加上一點西方世界流行的迷思,這些都令神秘的印度雅利安傳統充滿難以抵禦的魅力。
這導致對此現象充滿緊張情緒的經師群體反彈,開始抵制,雖然這種現象的始作俑者就是他們。由於這些年輕人所尋求的本就是所謂精神的覺醒,狂喜以及神通,還有對條條框框的反感,經師試圖通過這些途逕入手吸收發明神秘主義教義。例如,散射在新興理論下被合並成西方人想像中的印度瑜伽七個脈輪,盡管從散射本質來看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七脈輪本身就是從西方回流印度的產物;或是一種獨特的觀想技巧,通過誦念一些特別而缺乏含義的經咒,想像某些特別的圖案,來達到進入一種狂喜或出神狀態——這是美國經師阿耶卡普蘭(Aryeh Kaplan)根據瑜伽自己發明的傳統,他曾受到新紀元影響提出靈魂和鬼魂是一種電磁波,盡管他據說是物理博士出身。除此之外,這種對於傳統的發明還有很多,例如將聖經傳說中的祖先亞伯拉罕及其妻子與印度神毗濕奴及其妻子對比,得出二者背後的神聖奧秘一致的結論。
不過相比沒有傳承的瑜伽,新紀元以後的卡巴拉更受矚目,一種從美國回流到猶太人中的卡巴拉,並且非常受歡迎。這種卡巴拉不過是一種心靈雞湯,關注並引導所謂心靈的成長,讓人「認識到真正的人生目的是為以色列之神服務」從而學會自尊自愛,培養樂觀心態,以古老智慧給人帶來生活中所缺乏的快樂與幸福,並讓人更加快樂。這種膚淺而庸俗化並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神秘教導遍布各地,它以「猶太心理學」自居,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類「幸福生活的哲學」。
但上個世紀發生的事件,為整個猶太歷史,也包括猶太神秘主義歷史,留下兩個最深刻的財產。它們就是納粹集中營與以色列建國。
由於猶太人缺乏基督教對於世間之惡的靈活解釋,在猶太人看來世間任何事都是神的意志導致的,因此對於集中營的解釋大多維持在贖罪論上。人們說罪惡存在於這些猶太人或是這些猶太人的前世中,因此他們為了贖罪而被納粹殺死——贖罪論在猶太世界最經典的詮釋就是類似的主題,十個賢者被羅馬帝國處死,原因是他們前世是出賣了約瑟夫的十個兄弟,這一世受報。秉持這一說法的有不少是猶太社群中重要而知名的大師,但顯然公眾不能接受這一宣言,經常有世俗媒體抨擊這種言論。為了維護「所有事都是神決定的,並且神的決定都是好的」,還有更糟糕的解釋,例如認為大屠殺死者是罪有應得,是不干淨的,甚至還有認為是神為了避免他們以後犯下罪過導致他們不聖潔從而導致以色列族繼續在外流浪,而預先殺死了他們。當然,也有直白的說出「大屠殺的死難是為了以色列成立與最後的救贖而做出的必要犧牲」這樣的話的人。
猶太國以色列建立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按照神秘主義說法,救世主時代來臨前有幾個重要徵兆,其中一個就是猶太人聚集並建立以色列國。對許多以色列人而言建國是一個神學上的大事,一個宇宙進程上的大事,意味著神的奇跡出現,世界已經迎來巨大的神性變革。由此對以色列國的教團性詮釋非常多,甚至不少花邊小報擬定聳人聽聞的標題,專注於報導諸如《哈馬斯的火箭彈改變航道飛回去了!哈馬斯驚呼》這樣的內容——這些內容是真是假已經不重要了,重點在於這樣的信息正在人群中大量傳播。同樣大量傳播的還有批評猶太復國的言論,不過都是作為反例,是敵對的黑暗之子,應受詛咒的反猶反閃族主義者——猶太人在現下西方語境中獨霸了閃族這個詞,即使不少是哈扎爾人或是斯拉夫日耳曼後裔。而美國作為猶太人的樂園,第二家園,猶太人在這一樂土上享受作為選民應有的待遇,這個國家崛起並維護所謂世界秩序也意味著世界迎來了末世論的曙光。
但神越是在這個時代顯現保護猶太人的奇跡,卻越是與剛剛過去的時代所發生的慘劇形成鮮明對比。不過那已經不是現在的事情了,現在需要做的是拿著槍大踏步保衛巴勒斯坦這片土地,將黑暗驅逐出去,並在萬民的注視下修建聖殿,迎接救世主到來,好讓猶太人的救世主將猶太人重新放回至高的王座上,就好像預言的那樣:一開始是埃及,後來是巴比倫,再後來是羅馬,最後輪到以色列,並將永遠是以色列。猶太神秘主義從未想過拋棄自身的社會性,即使是天使的預言也是在指定這個民族命定的最終崛起。過去的一切都拋在身後,即將到來的救世主將擦乾淚水並為以色列戴上冠冕,那時曾經的犧牲都將值得。神皇川普庇護燈塔,天選之人內塔尼亞胡統領巴勒斯坦,王權已近在眼前,歷史已然終結。
在高歌下,人們圍著哭牆旋轉,火光中那未來將馴服世界的聖殿的影子在眾人面前越來越清晰,而那個曾經在哭牆下哭泣的黑衣女神,正坐在聖殿遺址中間,在滿心狂喜中等待即將實現的聖殿修建。槍枝與經書並舉,拯救的狂喜與犧牲的悲痛一起抓住人們的心靈,一個新的時代就要來了,那時犧牲的猶太人將復活,偶像崇拜者將被打入地獄,以色列將為王,猶太國的首都耶路撒冷將成為世界中心,救世主將君臨並統治這片漆黑大地。
在人們發出的高亢贊頌聲中,我聽見的只有神的無能與不義。

來源:機核